
文研论坛 |第81期
2018年11月27日晚上,“北大文研论坛”第八十一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学术的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对话”。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教授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郑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田耕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渠敬东
渠敬东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缘起。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作了题为《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学术)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为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为了纪念这篇一百年前的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为核心关切,编选了《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一书。该书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渠敬东、应星和田耕几位学者一同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以新书出版为契机,文研院与三联书店共同组织了相关学者来讨论韦伯一百年前提出的问题:“学术的天职”究竟是什么?

《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紧接着,渠敬东教授阐释了本次论坛的主旨,并从韦伯人格的力量和韦伯之问的价值这两个方面介绍了我们在今天纪念韦伯演讲的意义。渠敬东教授表示,本次论坛既要在韦伯的时代语境和思想脉络中理解他的思考与命题,同时又要在与韦伯的对话中直面中国当下的教育和学术的理念与体制困境,共同探讨中国学术的未来与可能。渠敬东教授认为,韦伯在《科学作为天职》所论述的一系列问题,直到今天都具有生命力,能够在今天致力于学术工作的人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并且这一系列问题并不仅仅属于德国,而是已经进入了世界历史的范畴,成为每个国家、每个文明养育的学者需要共同面临的时代处境。渠敬东教授表示,韦伯演讲的生命力一方面来自于韦伯的人格力量。韦伯作为一个以科学为天职的学者,拥有可贵的德性和直面时代问题的坚韧和勇敢,同时他在处理科学与政治的关联时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节制。另一方面,这种生命力来自于韦伯之问的价值。韦伯在一百年前富有前瞻性地指出德国大学的美国化问题,而这也是今天的科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在专业化作为科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的今天,我们如何处理价值与实践之间的巨大张力,如何面对思想生活与行动生活之间相互交织的永恒的困难?渠敬东教授认为,韦伯并没有在他的演讲中提供现成的、既定的或是可以模仿的路径,但是他的演讲对于我们仍有很多启发,可以帮助我们真诚地面对时代问题,探索出基于自身价值的路径。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李猛
第一位发言的是李猛教授,他梳理了韦伯发表《科学作为天职》的前因后果及该演讲在思想谱系中的位置。首先,李猛教授介绍了韦伯发表《科学作为天职》的背景。1917年11月7日,韦伯应慕尼黑学生组织的邀请发表该演讲。当时正处于一战末期,许多学子们对未来充满困惑,困扰于专业化、职业化的学术训练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希望韦伯能就此问题发表看法。其次,李猛教授简要介绍了演讲的内容。在演讲的前半部分,韦伯论述了职业的物质和外部意义,特别是德国高等教育的美国化趋势对于知识生产模式的影响。韦伯演讲的后半部分着力论述了职业的内在精神涵义,以及科学家应当遵守的伦理和自我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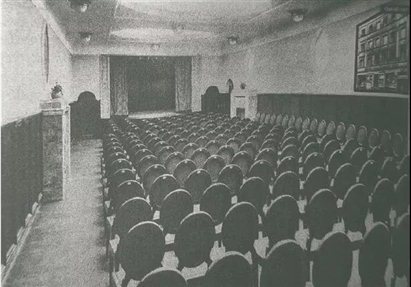
韦伯在1917 年11 月7 日发表“科学作为天职”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随后,李猛教授梳理了韦伯演讲发表及其演讲稿整理出版后在西方世界引起的两轮大讨论。第一轮讨论发生在一战与二战之交的激荡时代,讨论直指大学专业化分工的合法性根基。支持者赞同韦伯的教育理念,批评者则认为韦伯依然受限于专业化分工的“旧科学”,要求对高等教育体系进行彻底的反思并创立“新科学”。第二轮讨论则围绕着科学的政治后果这一主题展开。这一争论在1964年举办的纪念韦伯诞辰一百周年的研讨会上达到顶峰。在这次会议上,与会学者都十分尊崇韦伯的学术成就,但他们在韦伯的思想的政治后果这一问题上产生了针锋相对的意见——美国学者大多赞赏韦伯思想,将其称为战后的真正良心;而德国的许多学者却持截然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韦伯思想中有许多危险的元素,而这些危险思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德国从一战的废墟走向二战的灾难。李猛教授表示,这些围绕韦伯的讨论同我们今天的学术、教育和知识的世界仍有十分紧密的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 郑戈
第二位发言者是郑戈教授,他论述了韦伯意义上的科学是什么、科学的社会功用以及科学工作者面对的价值张力这几个问题。
郑戈教授首先解释了韦伯所谈论的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在中文语境下,科学所指称的一般是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家,韦伯所理解的科学也是以自然科学为模板,排除了神学、文学、法学等人文学科。也就是说,只有当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像自然科学那样关注事实和因果关系,才可以进入韦伯所理解的科学版图。其次,郑戈教授阐述了韦伯所理解的科学的社会功用。他表示,《科学作为天职》是韦伯对于在当时颇为受欢迎的浪漫主义“格奥尔格圈子”(George-Kreis) 的回应。“格奥尔格圈子”宣扬神秘德国,采用抒情而非自然科学的方法,尝试以所谓的精神气质来凝聚群众。彼时,德国青年人对于大学关注事实的教学方法产生厌倦,渴求能够引导他们进行价值选择的人生导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韦伯深刻反思了科学对于社会的功用,以及学术工作者在教育事业中应当遵守的伦理规范。郑戈教授认为,作为学界公认的、对于现代性体悟和研究最深的学者之一,韦伯可能并没有给出完美的答案,但他本人的一生极其深刻地承载和体现了这个矛盾。

格奥尔格圈子的核心人物 Stefan George
接着,郑戈教授进入到韦伯演讲的另一层问题,即大学教育中的价值问题。他认为,韦伯对于科学工作者的价值的论述存在深刻的张力。一方面,韦伯认为大学教师只能讲授关于事实与因果关系、行为与后果的关联的知识,需要客观地描述事实、摒除激情。但另一方面,韦伯也会认同理性只能为行动提供正当性,而激情才能提供驱动性力量。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言,“灵魂的欲望是命运的先知”。那么,该如何理解韦伯看似悖论的立场呢?郑戈教授认为,韦伯并非逃避价值判断;他关注的是价值与行动、行动与后果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价值选择本身。至于人们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价值这个问题,郑戈教授认为,韦伯并没有给出清晰的回答,而是将其留给个体去承担。许多学者由此认为,韦伯具有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倾向,将价值选择认为是神秘的,不可言说的。郑戈教授则认为,价值问题是韦伯学说中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需要放置在韦伯的整个思想脉络中理解:他后来提出的有关社会行动、支配关系和价值伦理的类型学就是为处理这一张力的所进行的尝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田耕
第三位发言者是田耕助理教授。他就韦伯思想中新教命题和价值理性化命题发表看法。他认为,韦伯作为精神贵族,对大学教育专业化的后果的深刻体悟,以及他所做出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令人动容。田耕助理教授指出了韦伯演讲中两个隐藏但重要的问题。第一,他认为韦伯发表演讲的目标听众并不是韦伯这样的学者,而恰恰是并不打算以学术为业的人。那么,学术对于不以学术为业的人的意义是什么?换言之,如何向不以学术为业的人讲述成为理智、诚实、热情且自律的学者的意义?第二,田耕助理教授认为,如何成为有理智和诚实的学者是比批判大学的科层式趋势更难处理的问题。当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切并不能被科学研究所解答,甚至要被科学研究击碎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们又如何坚守科学研究?

马克斯·韦伯,约摄于1907年
其次,田耕助理教授表示,韦伯演讲与新教命题有着重要的关联。他表示,韦伯展现出一种毫不妥协地为自己的价值负责的英雄形象,而这一形象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刻画的在世界边缘不断开拓的新教徒形象十分相似。然而,这也给我们带来造成强烈的困惑——如果今天的学者需要对价值负有责任且不断推进它,我们是否需要回到新教命题?再次,田耕助理教授论述了韦伯思想中的价值理性化命题。他表示,韦伯晚年最重要的学生卢卡奇曾就此问题做出了富有洞见的论述:韦伯预见了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趋势将导致极强大的非理性化力量的释放;非理性力量不是理性化的前提而是理性化的结果。在韦伯那里,价值是基于实践的喜好判断。韦伯并不认为有自然意义上的有价值的生活,而是强调价值是“吞食”知识之果的后果,因而拒绝在根本意义上通过科学作为天职提供行动意义。那么,如何将实践性的价值喜好变成坚韧的生命力量则是今天的学者需要面对的一个核心命题。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应星
第四位发言者是应星教授。他结合中国现代大学的教育变革发表对韦伯演讲的看法。首先,应星教授梳理了自蔡元培先生提出教育改革主张以来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变迁。他表示,蔡元培先生和韦伯是同时代人,他们对于大学教育的思考既有不同,也有着重要的关联。他表示,蔡先生借鉴了德国教育改革者洪堡的影响,而韦伯着力处理的是洪堡教育理念受到冲击后的德国大学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两人所面临的处境是不同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蔡元培先生改造传统的文人观念,建立专业化的现代教育体系,并需要面对科学职业化的后果,而这也正是韦伯的主要关怀。应星教授表示,学术与政治、学术与伦理、专与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张力逐渐浮现,但这些问题并没有在蔡先生的时代中得到彻底解决。他认为,经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时期,上述张力不断深化,成为今天的中国大学所面对的核心命题。
接着,应星教授论述了科学作为天职的内外之间的矛盾。他表示,面对当下充斥着浮躁气氛的外部环境,学者如何坚守内在精神显得愈加艰难。如何在外部环境和内在精神之间找到一个支点,是学者们面临的重要挑战。其后,应星教授讨论了韦伯演讲中提及的科学不能做什么。在韦伯那里,求真生活和求美生活之间是存在距离的,今天的学者已经难以将所有的美好追求集于一身。那么,如何将激情和纪律结合在一起,便需要学者们探寻以科学为业的人格力量。

应星教授对中国大学教育变革的研究:《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1895-192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宁
第五位发言者刘宁研究员从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化的视角论述了韦伯演讲的意义。刘宁研究员表示,自己从学生时代起,就受到韦伯思想的感召,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常常同韦伯进行对话,并谈及自己阅读韦伯演讲的几点感受。第一点,学术并不仅仅是浪漫的想象,而是要求我们接受严格的专业化训练。刘宁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在北大中文系接受的扎实、系统的学术训练,认为这跟韦伯演讲中论述的西方传统具有很多相似性。第二点,学术专业化也给学者们带来许多痛苦和困惑。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刘宁研究员反思了中国的学科专业化的后果。她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科专业化带来了理解中国传统学问的全新架构。然而,我们在总结专业化进程中取得的可喜的成就(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专题研究深化、学术组织建设的推进等)的同时,也需要面对专业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她认为,今天的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对于重要大家的研究严重削弱,存在各抱一隅、急功近利的现象。第三点,针对韦伯思想与中国的关联,刘宁研究员提出了牟宗三先生的儒家传统和余英时的史学传统之外的第三种视角,即中国古代的理性化进程。她表示,中国在唐宋之际的重大社会转型中经历了理性化加深的进程。诚然,这种理性化与韦伯所言的理性化不尽相同,但仍有许多相似之处。刘宁研究员提出,为了应对这种理性化带来的痛苦,唐宋士人做出了十分艰难的努力,理学的兴起和苏黄所做的文化创造都是其中重要的尝试。此外,刘宁研究员提出,中唐韩愈的《师说》是中国思想传统中十分重要的文本:韩愈提出了在天、地、君、亲之外的师道传统,为中国士人提供了新的存在方式,也为今天的学者提供了思想源泉,有望帮助学者们走出各抱一隅的困境。

潮州韩愈祠
自由讨论环节,学者们首先就世界学术体系与中国学人面临的处境进行讨论。渠敬东教授提出,今天的学术体系日趋专业化,然而具有文明传递意义的学术工作往往不能被转化成现有体系下的学术指标,学者们也被困在自己的生存节奏中面临人格扭曲的风险。这些是今日学者们共同面临的严峻考验。李猛教授认为,蔡元培先生在进行新北大改革的时候,面临着旧文明不能带来革新和进步的处境,尝试通过创新学术来拯救旧文明。然而,前者未必能带来期许的结果,反而可能与后者背道而驰。刘宁教授表示,我们需要在多个层面理解师道,师道不仅仅是师生之间的学术传承,也可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之间的精神交流。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打破求学、治学过程中“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艰难处境,创造出竞争之外的新的生存空间。田耕教授则认为,我们应该破除价值可以自动产生的迷思。他指出,纵观现代大学教育艰难困苦的历史,伟大的教育理想不可能是自动发生的。韦伯为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是:要想复兴文明理想,不仅要从其他的文明中进行切割,还要能够承接我们自身的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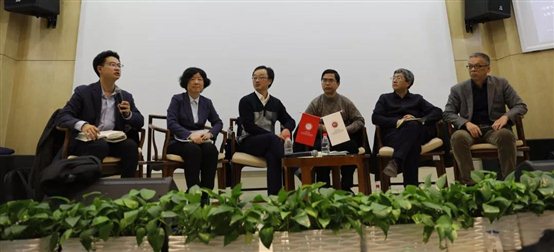
接下来,学者们就大学教育伦理的问题发表看法。渠敬东教授表示,在中国的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中,这几个元素是有内在连接的。中国自古以来是弘扬君子之学的国度,如今却面临着小人得志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大学教育中的伦理问题值得反思。李猛教授发表了对学者面临的严酷学术生态处境的思考。在学术专业化和标准化的趋势下,学术体系俨然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机器,学者作为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生产知识的工人。在这样的处境下,我们追问伦理在哪里的时候可能会无奈地发现,或许可以设定底线伦理,但却难以找到能够回答学术根本意义的价值伦理。应星教授认为,现在的考评体制将科研和教学分开,存在着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使得教学成为了“良心活”。此外,韦伯在演讲中强调的科学的禁欲立场也对今天的学者很有启发——学者不应当在课堂上灌输价值观念,而应该向学生展示价值选择的复杂性。郑戈教授认为,韦伯在演讲中对于教学中的伦理问题做出了很好的回答。韦伯提出,老师在课堂上不应该去迎合和谄媚学生,而是要帮助学生直面生活中的矛盾和艰辛。在韦伯看来,灌输价值观是廉价的,然而现实却是复杂的,实践价值观带来的后果可能与价值理想是矛盾的。此外,郑戈教授还表示,现代的大学之间可以存在一些分工,部分大学应该可以容纳部分摆脱学科分工束缚的学者,鼓励他们从事文明传承的工作。
最后,学者们就中国学者如何找到学术工作的价值基础进行讨论。刘宁教授认为,韩愈提出的师道传统对今天的学者也有启发。师道并不仅仅是技术意义上的教学,而是关涉个人与天地、人世的联系。刘宁教授表示,师道传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精神世界,成为许多新的思想观念得以生发的基础。李猛教授认为,专业化带来的考验的确残酷,但并非毫无意义——专业化的训练也是对学者是否对学术抱有持久热情的考验。然而,专业化对学者的成长也提出了巨大挑战——学者们如何在跨过了众多的学术门槛之后,依然相信学术的意义?李猛教授认为,学者们要想经受专业化训练的淬炼,却又不在学术训练中失去信念是困难的,这不仅需要学者自身的人格力量,也离不开老师的引导和友人的陪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