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7日,“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二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克武主持,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茅海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沛、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奇生做主题报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启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应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韩策参与会谈。
茅海建老师以“清代的驿递、书信、电报与《缙绅录》——‘信息渠道与国家秩序’”为题带来第一场报告。清朝之所以能够管理广阔的地域范围与众多人口,正是因为有着相当畅通的“信息渠道”,其基本形态就是驿站系统。清代相较于明代增加了许多驿站,并将驿站开支纳入国家的财政支出。清代的驿站系统是十八世纪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办交通系统。驿站系统的主要设施是驿道,最大的开支是养马,负责的主要工作是官员的交通和公文的传递。清代驿站系统运作情况大致良好,尤其是乾隆朝,之后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在公文传递方面仍然保持较高的效率。但是,正因为清代的驿站系统只开放给官方免费使用,随着时间的流逝,驿站系统的效率也渐趋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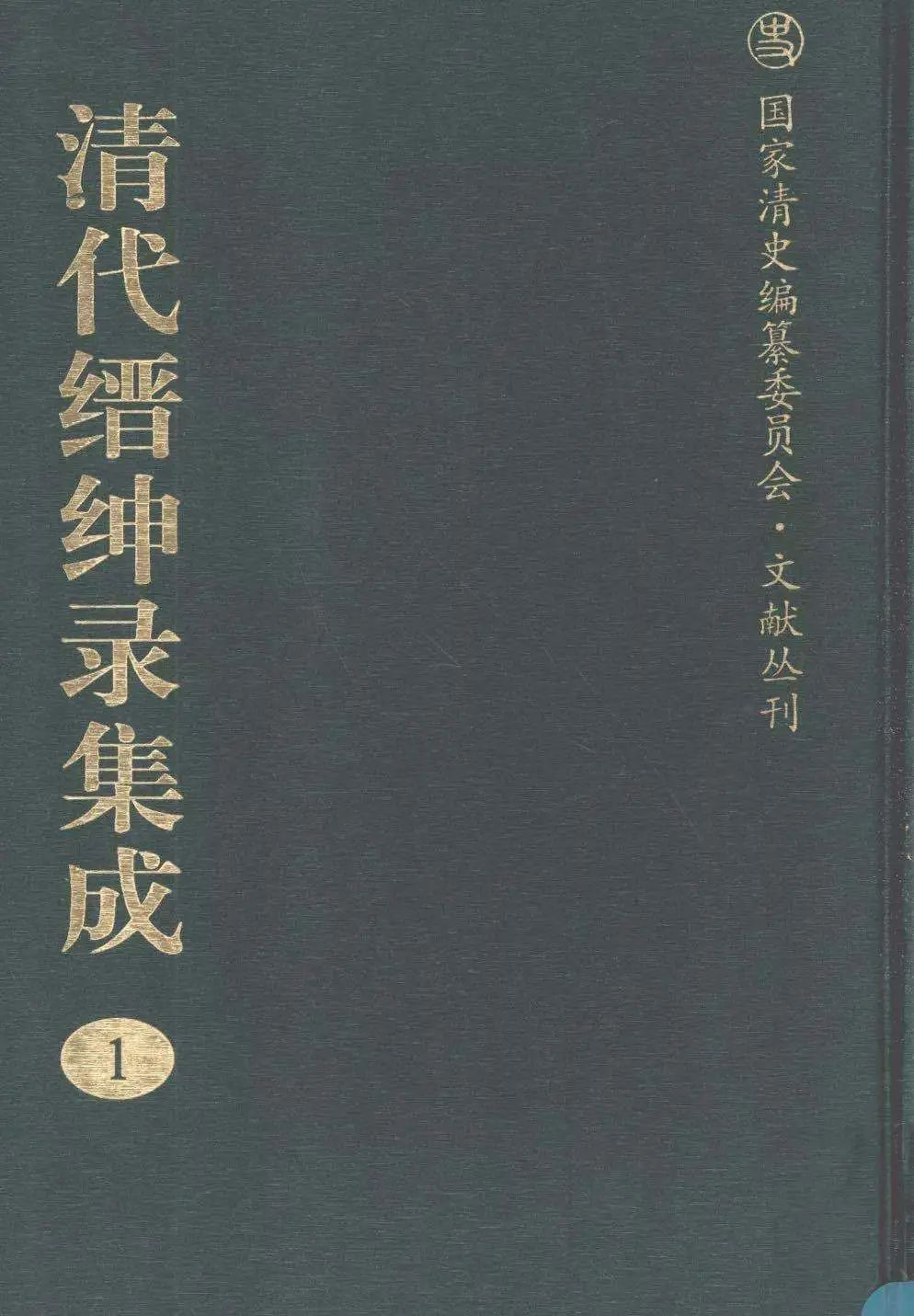
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全9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茅海建老师进一步指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情况也逐渐发生变化。通商口岸在沿海沿江建立,技术革命的开展使得铁质轮船取代风帆动力木质帆船,这两个变化改变了中国的经济成分与社会结构,原来的民信局很快发展起来。大清邮政建立前后,中国进入了铁路建设的高峰期,这也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十九世纪另一个重大技术革命是有线电报。在西方的压力下清政府铺设了三大电报干线,与丹麦资本的大北电报公司和英国资本的大东电报公司接通。清朝兴建的电报系统,大多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而官办电报主要用于军事用途,但也对民众开放。茅海建老师总结,清末已经有了两个信息渠道系统:原有的驿站系统与新建的通信电报系统,而新系统必将取代旧系统,官员上任不再使用驿站系统,电奏、电旨也开始出现,官员之间信件与电报大规模增加,直到最后驿站系统消亡。原有的驿站系统只有一个信息中心,即北京,而新建的通信电报系统变成了多个信息中心,最大的中心转移到了上海。这一发展使得信息更多元,传播速度也更快。
茅海建老师指出,清代人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方式是邸报。这在宋代已经形成了相关制度,明清两代皆继承之。邸报最重要的特点是其商业性,民间的印刷量甚大,官员和人民可以订阅,还出现了以月汇编的邸报合集。《缙绅录》是民间出版的全国官衙官员人名的手册,其中包括从京官到地方官,各个部门官员的官职、姓名、字号、籍贯、出身等。人们可以通过邸报获得官府政策信息,还可以通过《缙绅录》获得官员信息,从这个角度看,清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相当可观。茅海建老师认为,清后期的诸多“信息渠道”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对外信息获取上的缺乏,这不仅仅关系到“国家秩序”还关系“国家安全”。
接下来,江沛老师以“近代媒体与五四运动的空间转换”为题带来第二场报告。江沛老师以“现代民族主义运动,何以由五四而起”发问,引入报告。清末以来,中国有三次对外的重大事件——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山东问题,其损失渐小,但抗议却渐强,这是为什么?江沛老师认为,正是在20世纪初传媒技术革命性的展开,对于信息的传播与民族主义的奠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得五四运动成为可能。电报的出现完全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导致不同区域的人接受了同一信息,感受到个体与群体的共存感,形成近似的思维。近代的印刷机引入中国,报刊、书籍批量印刷,知识的廉价复制使得信息的快速传播成为可能。交通、邮政、新式学堂的建设,以及辛亥革命后政治宽松的氛围等,都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和空间。所有的因素汇聚起来,构成五四运动开展的基础。
江沛老师以巴黎到北京的信息传递为例进行说明。从鸦片战争到一战结束,民族危机成为知识精英最为敏感的考量。为了参加巴黎和会,北京政府做了积极的准备,当时巴黎与北京之间的信息传递是通过电报进行的。梁启超通过电报将山东问题归罪于曹、陆、章等人,林长民据此撰“代论”,发表后舆论沸腾,促成了五四运动。助推五四学潮持续发展的有明暗两种力量,一条是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怀,这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和心理感染,另一条是诸种政治力量在对学潮的充分利用中助推运动向全国蔓延,意在形成一条配合政争的舆论力量。两种力量借助由电报、报刊、邮政和新式交通构建的信息与人员的快速流动,持续发酵,欲罢不能。当运动从北京传到上海,上海的经济结构使得运动以罢工、罢市的形式发展。上海罢工需要得到帮派的同意,帮派的动力在于抵制日货以为国货开辟市场。上海的“三罢”迅速波及内陆,其中凡是反对皖系的地方,学生运动都得到了迅速扩展。
江沛老师指出,在五四运动期间,北京与各地进行了多方的政治博弈,这一博弈主要是通过电报展开的。围绕签约,亚洲和欧洲之间也在进行信息上的反馈。政府和代表团围绕签约的态度变化也是通过电报进行的。因为巴黎信息在国内的传递,使得这一问题被摆在了全民视野之下,因为情感、道德、利益的纠缠,中央政府的选择就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吴佩孚通过持续的通电树立了“革命将军”形象,其政治影响力也得到了扩张。
江沛老师总结到,传媒技术奠定了五四爆发的必要前提,民族情感推动五四学潮的勃发,政治势力从中推动,学潮扩散为“三罢”影响渐广,利益选择及民众压力终致代表团拒签合约。从洲际信息传递、运动中心的南北交替、政治势力跨越空间的电报战直至国内政局对于签约与否的影响,都是经历在传媒技术的基础之上。五四运动是一场以传媒技术为基础,融合国际因素、国内政局纷争、民族主义高扬、工商群体登台的历史大戏,是新旧因素的复合体,是现代中国社会运动的新起点。
王奇生老师以“联络技术与权力机制——莫斯科与中共革命”为题进行报告。王奇生老师的报告涉及1920年到1940年这一时间段,以“莫斯科”代称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二者密不可分,很长一段时间共产国际掌控在苏俄政府手中。共产国际是第三国际,与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在组织的运作方式上完全不同。当列宁组织成立共产国际时有一个总体的构想,即建立一个世界的共产党以进行一场世界革命并最后建立一个世界苏维埃共和国。共产国际不是一个松散的各国共产党的联盟组织,而是一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成立后派人去各国帮助建立共产党。各国共产党不是独立的,它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组织方式是高度的集权与铁的纪律,即各国共产党的行动都需要绝对服从共产国际的指挥,包括最高人事、路线方针、行动计划,乃至是错误的决定,并接受共产国际特派代表的直接监督与就地指挥。

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今上海福康里九号)
由于电报费用过高,初期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主要通过书信进行联系,这就会导致信息沟通的不畅。各国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各国国情千差万别,而莫斯科强调各国共产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命令。这就使得各国共产党经常陷入尴尬的境地,即有时必须执行莫斯科发来的时过境迁的命令。当时莫斯科对中国情形所知有限,命令又经常过时,还要求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统一行动。这使得莫斯科的命令与中共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很大矛盾。直到1930年初期,莫斯科与上海中共中央之间建立了直接的电台和电报通信,信息的沟通才变得通畅。不过,新的问题又来了,通讯技术改善以后,也导致了莫斯科对于中共的控制大大加强,中共的自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中共中央对莫斯科更加亦步亦趋,难以施展自己的手脚和发挥自己的独立自主性。长征开始后,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电报密码丢失,这样在长征时期,中共一度失去了和莫斯科的联络,反而为毛泽东的自主决策提供了空间,也为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机会。等到长征结束后莫斯科与中共的通讯重新建立,莫斯科只能够承认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已确立的重要地位。
另一方面,莫斯科也越来越认识到高度集权、统一指挥的局限,所以共产国际七大后,莫斯科也逐渐放松了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这也为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提供了较大空间。到抗战中后期,毛泽东个人直接控制了与莫斯科的电报密码,进一步掌控了与莫斯科联系过程中的主动权。王奇生老师还补充到,毛泽东在长征时期运兵如神,也和当时中国共产党能够破译国民党和地方实力派的电报有很大关系,当时党内的报务人才大多是从莫斯科培训回来的。到抗战时期,在国、共、日三方的电报战中,日本电报技术强于共产党,共产党又强于国民党,这使得国民党有时在战场指挥上,因害怕被破译而不敢使用电报。从信息沟通的角度看,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中共既有从莫斯科获得经济、技术支持的一面,也有受到莫斯科掣肘的一面。
随后,论坛进入评议环节。唐启华老师指出,近代以来中国被纳入以西方为中心的文明之下,并被西方世界纪录下来,产生了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又影响了中国。外部的信息始终对中国影响很大。研究中国史,一定要用到外国的材料。比如中国近代史研究一直受到西方学界提供的档案影响,如英国档案、外国传教士的档案等。而1919年除了五四运动、共产国际的建立之外,6月28日国际联盟的创生也是相当值得关注的一点。
唐启华老师主要对江沛老师的报告进行评议,他认为除了考虑到传媒技术对五四运动的影响,还应该纳入国际背景的视野,即表面上巴黎和会的争端是中国和日本的竞争,实际上是美国和日本的竞争。美国支持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诉求,中国代表团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的。此外,巴黎和会召开时一战刚刚结束,从北京到巴黎的电报并不畅通,当时主要是通过太平洋的水线,通过美国到巴黎。当时电报发送的速度时快时慢,从北京到巴黎一份电报慢时需要七八天,快时也要一二天,而电报发送速度最慢的时候正好是在五四运动。学界普遍会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因为当时很多人知道了巴黎和会把山东半岛的权利直接交给日本,但是北京政府5月7日才收到相关电报,5月9日这一和会的结果才见报,因而五四运动的参与者不可能是因为知道这一事件才进行抗议的。电报和五四运动的关系,可能还要再做更细腻的考证。
唐启华老师还补充道,有一种说法认为6月27日北京政府发出“不要签”的电报是“废电”,因为该电到达巴黎时早已签约,真正决定不签的,应该是代表团自己,而非北京政府。但就北京政府的主观意图而言,要说这是“废电”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即北京政府需要知道28日下午3点签约,但是相关往来电报上巴黎代表团没有提及具体签约时间。所以这是不是废电,还要再考虑。此外,当时的报纸中有各种各样的舆论来影响大家对该问题的看法,这一部分还可做深入的探讨和研究。

1919巴黎和会
接下来,应星老师进行评议。他指出,王奇生老师进入中共研究的角度可能反映了他对现有的党史研究的批评。王奇生的研究有两个特点很明显,第一,他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中共早期而非成熟时期。这个视角很有见地,对于帮助我们摆脱成败的观点来探讨问题相当重要。中共经历的各种曲折和分岔对于历史研究相当重要,其中政治文化的制度渊源,对于理解后面的流变有根本性的影响。第二,以往的党史研究集中在政治、制度、大人物,缺少对实际的运作机制的研究,而王奇生主要落实在实际的运行机制上。王奇生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研究基层的运作,这开拓了风气,但是这种研究也可能和高层的运作存在断裂。王奇生如今转向了高层的研究,即研究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沟通机制,这就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上下运作,而且能使我们看到中共微观和宏观的联结点。
应星老师指出,我们要看到共产国际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共产国际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并且注重国家的地位,这与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是不同的,但是在阶级中心和欧洲中心上则与之相同。然而中国共产党天然地存在工人阶级的弱项,以民主集中制运行的共产国际必然会对中国有着复杂的影响。此外,应星老师认为,上海和中央苏区有一个没有被破坏的水上交通线,直接沟通了上海中央和中央苏区。这也是二者沟通很通畅的一个原因。在北京和上海,中共崛起的方式很不一样,在北京的崛起和北大有关系,在上海则和上海的通讯有关。陈独秀始终坚持在上海,和上海作为信息通讯的中心是分不开的。
韩策老师对茅海建老师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他认为,电报的产生和流行在晚清影响非常大。晚清有一个书信时代到电报时代的过渡,如从政治大员的文集当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胡林翼时代没有电报,李鸿章、刘坤一则电报和书信互用,书信占很大部分,而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后来基本上多用电报。随着技术的改进,官员之间的沟通大规模增加了。之前是一个单线沟通渠道,现在各地官员和京官,还有各地区官员的电报沟通,形成多线性的信息渠道。于是中央对地方的了解增加了,而地方对中央的了解增加得更多。因为各地官员之间联系密切多了,这使得地方官员更容易形成联盟,加大了中央使用密折制度牵制地方的难度,由此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韩策老师在茅海建老师提出的晚清信息中心从北京到多渠道信息中心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秩序的影响。上海作为信息中心的崛起,首先是五口通商的结果,后来盛宣怀把电报总局设在上海,以及上海的中外新闻媒体的繁荣都是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上海不仅沟通着内地、北京和海外的信息,而且信息沟通的数量和效率比以前有了几何级的增长。这些信息都是资源,有些核心信息甚至意味着权力。上海信息中心、经济中心的形成,在庚子之后越来越对北方朝廷形成挑战,对南北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韩策老师还指出,《缙绅录》的出版确实反映了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但是这与十九世纪欧美那些报刊比较发达,崇尚言论自由,有代议制的国家比起来,还算不上政府信息公开很高。清末立宪之后,政府信息比以前公开了很多,并为北洋政府继承。这一方面因为清朝政府确实有不少人认为政务应该公开,另一方面也是形势倒逼的结果。韩策老师补充道,收藏《缙绅录》最多的是北京大学古籍库和国家图书馆,但是只有清华大学图书馆将其所藏《缙绅录》影印出版,供学界方便利用。目前,李中清教授的团队正在做一个《缙绅录》数据库。

工作坊直播现场
随后,几位主讲人对评议人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茅海建老师补充,除了五口通商的影响,上海是在北京不愿意做信息中心的时候做了信息中心,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而关于信息公开程度的评价,他认为,清政府是中央集权制的,在这一制度体系下,很多信息并不需要公开,而非不愿意公开。清政府在内部的信息沟通和传递上没有问题,它最大的问题是对外部信息获取不足。针对唐启华老师认为的学生更多抗议的是不公而非巴黎和会外交结果的观点,江沛老师指出,从5月4日北京学生给美国外交部的陈词来看,学生明确要求青岛归还中国,似乎学生是清楚了解巴黎和会的结果的。王奇生老师补充认为,中共内部的信息沟通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广东省委和上海中央联络之中,也存在着同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联络时一样的问题,即中央高度集权,地方缺乏自主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