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10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九次)在北京大学111会议室联合线上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欧树军做主题报告,题目为“美国往事:塞缪尔·亨廷顿的政治学思”。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包慧怡、陈文龙、杜华、梁云、刘清华、陆一、罗鸿、王明珂出席,包伟民、谷继明、焦南峰、刘文飞、山部能宜、盛珂、赵丙祥线上与会。

讲座伊始,欧树军老师指出,对于当代世界而言,美国的镜鉴意义依然不容忽视。也是因此,过去数年来,欧老师始终将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这位美国政治学家作为分析窗口。就对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的影响而言,亨廷顿可谓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学家之一。通过对其生平往事与政治学思考的历史考察,当能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国家性质与政治学发展轨迹。故而本次讲座的核心是亨廷顿对美国政治的长期观察与深入思考,欧树军老师将其概括为“党、侍、军、霸、旧、弱、骄、教、傲、诡、虚、裂”十二个关键语词。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欧树军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一个中产家庭,16岁考入耶鲁,三年后以特优成绩提前毕业;1947年考入芝加哥大学读硕士,1年后毕业。彼时,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重镇。1948年亨廷顿赴哈佛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这一时期,他对美国政治的理解可用“ ![]() ”来概括,即美国政党政治。美国建国者并未预想到政党政治的出现,就此而言,美国宪法堪称“三无”宪法——它既没有政党条款,也缺乏军事条款;对联邦政府的运行也未做出明确规定;从1776年独立建国到1951年杜鲁门时代,对美国总统的任期也没有限制。
”来概括,即美国政党政治。美国建国者并未预想到政党政治的出现,就此而言,美国宪法堪称“三无”宪法——它既没有政党条款,也缺乏军事条款;对联邦政府的运行也未做出明确规定;从1776年独立建国到1951年杜鲁门时代,对美国总统的任期也没有限制。
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关切,贯穿亨廷顿的一生。他从政党政治之社会基础的代际更替角度指出,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政党政治经历了一个由“新政联盟”到“少数派”、“独立派”的三代更迭。小罗斯福时代组建的“新政联盟”主要由城市劳工、中产阶层、南方白人、新移民等群体构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黑人、青年人、妇女、自由派知识分子、西班牙裔等构成的“少数派”崛起。被称为“独立派”的“婴儿潮一代”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三代政治力量先后主导了美国政治直至今日。对民主、共和两党而言,若要谋求政治联盟,要么向下深耕“少数派”,要么向外吸引“独立派”,舍此少有他途。随着族群、阶层、性别、职业等“功能性组织”日趋重要,社会群体更加碎片化。两党共同面临的危机在于,当“新政联盟”已然瓦解,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有国家领导能力的政治家群体,来逆转社会群体碎片化趋势?是否还可以在碎片化情势下重建跨阶层联盟,并推出新的具备长期吸引力的国家发展目标?

“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反越战示威中的嬉皮士
1967年4月15日
在整个50年代,亨廷顿的政治学思考主要体现在“ ![]() ”与“
”与“ ![]() ”两个关键语词上。前者为“侍从主义”。在比较考察了美国州际贸易委员会等部门后,亨廷顿发现,政府部门的专业化越强,自主性反而越差,越容易受到“侍从主义”影响,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他的学生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等书中,对美国政治衰败根源的分析同样建基于此。“军”指代“军-政关系”或“文-武关系”问题。二战让美国拥有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队,1951年朝鲜战争与1955年越南战争则进一步扩张了军方势力。在此背景下,亨廷顿成名作《军人与国家》于1957年正式出版。他从现实保守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自由主义的美国社会必须接受一支强大部队的存在,同时也强调军官必须坚持保守主义的职业伦理,服从文官权威、接受文官控制。
”两个关键语词上。前者为“侍从主义”。在比较考察了美国州际贸易委员会等部门后,亨廷顿发现,政府部门的专业化越强,自主性反而越差,越容易受到“侍从主义”影响,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他的学生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等书中,对美国政治衰败根源的分析同样建基于此。“军”指代“军-政关系”或“文-武关系”问题。二战让美国拥有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军队,1951年朝鲜战争与1955年越南战争则进一步扩张了军方势力。在此背景下,亨廷顿成名作《军人与国家》于1957年正式出版。他从现实保守主义的视角出发,认为自由主义的美国社会必须接受一支强大部队的存在,同时也强调军官必须坚持保守主义的职业伦理,服从文官权威、接受文官控制。
自1967年撰写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System of World Order一文开始,“![]() 权”问题正式进入亨廷顿的思考。他认为二战后的美国只是替代了欧洲留下的权力真空,再过二三十年,美国或将同样遭遇霸权更迭的规律,非西方世界国家或将取而代之,填补美国衰败留下的权力真空。亨廷顿做出这一判断时,美国尚处于战后繁荣期间。次年,《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出版,成为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最富影响力的论著。他在此书中把美国视为一个“新社会、
权”问题正式进入亨廷顿的思考。他认为二战后的美国只是替代了欧洲留下的权力真空,再过二三十年,美国或将同样遭遇霸权更迭的规律,非西方世界国家或将取而代之,填补美国衰败留下的权力真空。亨廷顿做出这一判断时,美国尚处于战后繁荣期间。次年,《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出版,成为亨廷顿在美国政治学界最富影响力的论著。他在此书中把美国视为一个“新社会、![]() 国家”。“新”指新教,美国社会身份平等,其源头是英国的新教革命。而在政治上美国却是个“旧国家”。看似权力分立,实则职能混同,自政党、军事、行政至国家元首,总统一身四任。总统作为自然人不可能同时具备四种能力,由此便不得不借助智囊、幕僚履行职责,这就导致现代美国复活了古老英格兰的都铎制。
国家”。“新”指新教,美国社会身份平等,其源头是英国的新教革命。而在政治上美国却是个“旧国家”。看似权力分立,实则职能混同,自政党、军事、行政至国家元首,总统一身四任。总统作为自然人不可能同时具备四种能力,由此便不得不借助智囊、幕僚履行职责,这就导致现代美国复活了古老英格兰的都铎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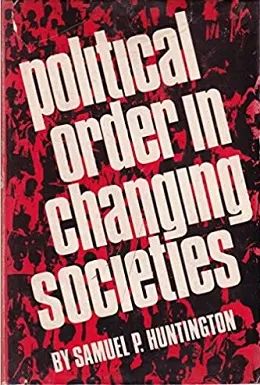
《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首版封面
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
时间进入70年代后,亨廷顿将研究重心集中在了民主危机与政治参与上。亨廷顿指出大众参与诉求高涨、美国民主制的回应性和统治能力变![]() ,政党政治效能由此下降,政治参与率随之降低,久而久之美国民主将出现巨大的统治能力危机。他认为有必要降低人们对民主的期待,将其仅作为“建立权威的手段”,这可谓是“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之先声。1975年完成的《难以抉择》一书虽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但亨廷顿的判断基础依然源于美国政治现实。在他看来,美国主推的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傲
,政党政治效能由此下降,政治参与率随之降低,久而久之美国民主将出现巨大的统治能力危机。他认为有必要降低人们对民主的期待,将其仅作为“建立权威的手段”,这可谓是“民主的马基雅维利”之先声。1975年完成的《难以抉择》一书虽然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但亨廷顿的判断基础依然源于美国政治现实。在他看来,美国主推的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傲![]() 地过度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现代化意义,相信“美好的事物会一夜之间同时到来”。对于非西方世界而言,参与往往只是手段,或者现代化发展的副产品,个人对流动或组织两种参与模式的选择,受制于政治参与的层叠效应。
地过度强调公民政治参与的现代化意义,相信“美好的事物会一夜之间同时到来”。对于非西方世界而言,参与往往只是手段,或者现代化发展的副产品,个人对流动或组织两种参与模式的选择,受制于政治参与的层叠效应。
80年代是亨廷顿政治思考的一个转折阶段。从1981年出版的《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开始,亨廷顿关注的重心转向对重大政治社会困境的道德关注,他试图找到制度背后的文化要素,“![]() ”的意义渐次凸显。亨廷顿认为界定美国政治核心的并非自由主义社会共识,也非贫富阶级冲突或利益集团,而是“信念政治”,而其源头在盎格鲁-新教文化。在1987年完成的《发展的目标》这篇小文章中,亨廷顿指出美国不应盲目自信,过于“
”的意义渐次凸显。亨廷顿认为界定美国政治核心的并非自由主义社会共识,也非贫富阶级冲突或利益集团,而是“信念政治”,而其源头在盎格鲁-新教文化。在1987年完成的《发展的目标》这篇小文章中,亨廷顿指出美国不应盲目自信,过于“![]() 慢”,将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强行作为指导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核心原则。需要看到一点,世界不同地区存在极大的文化差异,由此也催生了不同的“美好社会”构想,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当80年代渐入尾声,世界局势风云突变。亨廷顿于这一时期出版了《第三波》一书,讨论了20世纪晚期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他一方面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同时也强调全球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民主事实上成为了维护美国世界利益的工具。此为
慢”,将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强行作为指导其他非西方国家的核心原则。需要看到一点,世界不同地区存在极大的文化差异,由此也催生了不同的“美好社会”构想,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当80年代渐入尾声,世界局势风云突变。亨廷顿于这一时期出版了《第三波》一书,讨论了20世纪晚期的全球民主化浪潮。他一方面指出,民主是个好东西,同时也强调全球民主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民主事实上成为了维护美国世界利益的工具。此为![]() ,布热津斯基因而名之以“民主的马基雅维利”。
,布热津斯基因而名之以“民主的马基雅维利”。
1991年,苏联解体,“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作为对相关讨论的回应,亨廷顿完成并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在这本影响甚大的论著当中,亨廷顿对美国政治的核心判断可作如下概括:作为基督教文明的核心领导国家,美国的实力已经衰落,外强内![]() 。若不甘失落,又坚持白人至上的以种族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明,强行推广自己的所谓优越文明制度,将成为文明冲突的真正根源。
。若不甘失落,又坚持白人至上的以种族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明,强行推广自己的所谓优越文明制度,将成为文明冲突的真正根源。

柏林墙倒下
新世纪的钟声尚未落定,“9·11”的烟尘便降临至纽约,美国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在这一背景下,年逾八旬的亨廷顿完成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书中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冷战之后美国的历史命运。罗马、不列颠和苏联的解体终局是否将成为美国的宿命?去美国化与美国化的“文明冲突”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美国成为一个分![]() 的国家,成为一个陷入激烈党争的现代社会。当此之时,美国又该何去何从?在“世界的美国”(自由主义的)、“美国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与“美国的美国”(民族主义的)三个前景之间,究竟应当如何抉择?在亨廷顿看来,应当让美国成为美国,使其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惟其如此,未来之事方可徐徐图之。
的国家,成为一个陷入激烈党争的现代社会。当此之时,美国又该何去何从?在“世界的美国”(自由主义的)、“美国的世界”(帝国主义的)与“美国的美国”(民族主义的)三个前景之间,究竟应当如何抉择?在亨廷顿看来,应当让美国成为美国,使其能够保持自身的独特性,惟其如此,未来之事方可徐徐图之。
最后,欧树军老师总结道,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接受研究生教育起,亨廷顿始终活跃在美国政治学界,著述不断。透过亨廷顿,我们既能看到美国政治学界的历史变化,也能发见美国政治的时代变迁。

论坛现场
在接下来的交流环节,与会学者针对亨廷顿思想及其影响的研究层次区分、美国的宗教性及其在建国思想的位置、陷入激烈党争的现代社会困境以及大国博弈背景下重新定义文明的必要性和适用性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