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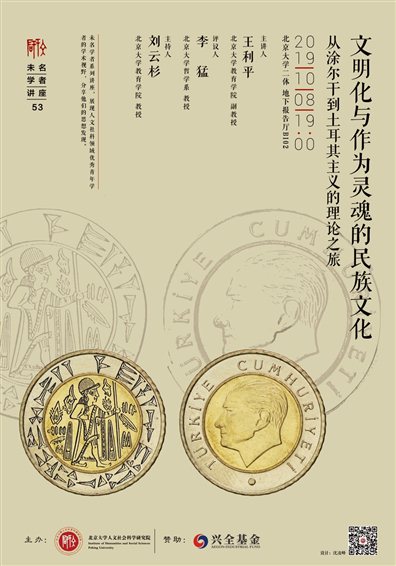
2019年10月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三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文明化与作为灵魂的民族文化——从涂尔干到土耳其主义的理论之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利平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评议。

讲座伊始,王利平副教授首先讨论了民族(nation)界定的问题。她指出,有三种定义民族的方式值得关注。第一种方式以地理疆域为界,从领土、边界、国家主权的角度出发,把民族定义为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领土之上的人民整体;第二种方式形成于法国大革命之后,重视基于公共政治参与的抽象身份认同,不强调原先的种族、血缘差异;第三种方式则形成于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之后,与法国式的普遍主义民族观念相对,将民族理解为以种族和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强调族群的纯正和历史溯源。以此为基础,民族主义便可区分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Political Nationalism)和种族、血缘上的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前者以法国和英国为代表,将民族看作想象的共同体,依赖强力的现代国家来维持抽象公民认同和政治参与;后者依托种族、血缘来建立民族,但容易催生集权,且一旦国家失败、政治认同无法确立,就会带来种族杀戮或者极端冲突。此二者的对立也一定程度在地缘上体现为西欧与非西欧的分野。
作为成长于普法战争后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始终关心着民族与民族国家的问题。尽管法国的民族主义通常被看作抽象政治认同的代表,涂尔干却恰恰认为个人意义上的身份认同不足以建立一个民族。这便呈现出涂尔干与土耳其主义的关联。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在面对民族主义时,仅仅处理种族、血缘上的问题往往是不够的,前文的两种民族主义在实践中并非二选一的绝对关系;另一方面,土耳其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卡尔普也直接受到了涂尔干的影响。因此,理解涂尔干对格卡尔普理论资源的传导逻辑便十分重要。

王利平副教授从两个角度梳理了这一传导关系。首先是涂尔干所讨论的民族构成问题。通过在德国的考察,涂尔干指出,要想了解民族情感和爱国信念,就需要通过国民教育,即根据事物的自然原则去了解构成爱国信念的要素。涂尔干认为,人的人格是社会生活、社会存在的产物,个人无法脱离社会,民族则是构成人格的群体之一。人所必须拥有的集体情感便是爱国信念的基础。构成人类社会的不同群体中,家庭是最基础的,其上存在部族、族群等,而民族(nation)则是这些群体之上更高级的存在,与政治社会相对应,拥有强大的政治中心和具备反思性的集体意识,不能被向下化约。其次是涂尔干对民族与世界主义关系的讨论。涂尔干并不否定普遍人性的可能,但他同时认为,普遍人性自身无法构成一个社会,也无法搭建道德共同体。因此,人可能生活的最高程度道德共同体就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各民族则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加入普遍人性、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外,格卡尔普所处正值奥斯曼帝国瓦解、逐渐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年代,身处帝国形态与西方民族国家形态两种世界主义的夹缝之中,处境相较法国同期更为复杂。在此背景下,早年的格卡尔普支持奥斯曼主义,即以奥斯曼帝国为形态,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给予帝国内部各宗教、族群更为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打造奥斯曼-伊斯兰民族;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对愈加强大的民族主义影响,加之意识到作为帝国的奥斯曼已然不可能保持同从前一样完整的疆域,格卡尔普转向了土耳其主义。
.png)
作为土耳其民族主义的表现形态,土耳其主义是奥斯曼帝国从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民族主义思潮。从格卡尔普对土耳其主义的论述中,可见其受到了涂尔干相当的影响:格卡尔普将土耳其主义所期望建立的土耳其民族称为“社会”(society),拥有更集中、更清晰的集体意识,可以与爱国主义相对应;而与之相对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图兰主义则仅构成“共同体”(community),集体意识在其间是弥散的。在格卡尔普看来,作为社会的民族不同于动物范畴的“人种”(race),亦高于作为载体的“族群”(ethnic),其并非个体的自愿决定,而是个体在社会的文化和教育中所吸收的情感方式。
此外,涂尔干对格卡尔普的影响也体现于民族观的进步性(progressive)上。这一时期的土耳其知识分子深受18世纪后于欧洲兴起、以语言学方法为工具的突厥学影响,但格卡尔普则在承认这一作用的基础上,反对去除奥斯曼语言中受波斯语、阿拉伯语影响的部分,不提倡还原“未经沾染”的突厥文化本源。
随后,王利平副教授详细阐释了格卡尔普在当时政治思潮中的观点。在对图兰主义的辨析中,格卡尔普认为,图兰不等同于土耳其,前者涵盖的范围更加广泛﹙见侧图﹚,只能作为精神上乌托邦式的种族共同体存在,而无法带来实质的民族。 同样,虽然伊斯兰信仰对土耳其而言是重要的精神资源,但在格卡尔普的观点中,泛伊斯兰主义亦不可构成民族,而仅是宗教群体。讨论奥斯曼主义时,格卡尔普则指出,精英阶层的突厥人在文化品位上已经被奥斯曼文明归化了,因此,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改革措施只能触及上层精英,无法在道德和价值上重新为一般的土耳其民众带来活力,进而不能在实质意义上塑造一个土耳其民族。 同样,虽然伊斯兰信仰对土耳其而言是重要的精神资源,但在格卡尔普的观点中,泛伊斯兰主义亦不可构成民族,而仅是宗教群体。讨论奥斯曼主义时,格卡尔普则指出,精英阶层的突厥人在文化品位上已经被奥斯曼文明归化了,因此,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改革措施只能触及上层精英,无法在道德和价值上重新为一般的土耳其民众带来活力,进而不能在实质意义上塑造一个土耳其民族。
最后,王利平副教授总结了格卡尔普对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的辨析。在格卡尔普的观念中,文明和文化在要素上是相同的,其区别在于:文明具备扩张性、带有世界主义倾向,是可以被传播、模仿、转借的;文化则是民族在自然演变过程中逐渐积淀的集体情感与信念,无法被习得。借助这一区分,格卡尔普希望说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许多改革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没有看到民族的文化特性,而改革所借鉴的文明要素则未能在民族形态中扎根。这正是格卡尔普强调土耳其主义的原因:他认为,首先要拥有民族这样的共同体、拥有健康的道德生活,才可能迎接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

评议阶段,李猛教授指出,格卡尔普实际将涂尔干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对比,后者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的影响,涂尔干则认为构成社会的真正核心是一种集体意识或集体情感。由此可见,涂尔干和康德的理想差异之处正在于,康德认为世界大同的共和国有可能达到,而涂尔干则认为这样的世界共和国没有道德共同体作为基础、缺乏社会内容,因而是不可能的。
接着,重新梳理格卡尔普的分析思路后,李猛教授指出,土耳其的现代策略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在于,古老的东方文明应该如何在现代社会继续存在,其选择又受到何种限制?在宗教与民族间,格卡尔普选择了后者。从结果来看,奥斯曼的“世界主义”令人不安,但人们并未对康德式世界主义抱持过强敌意。所以,格卡尔普选择土耳其主义是否可以被视为希冀获得世界政治接纳的一种尝试?而另一值得思考的问题:人们今天为何仍会对民族主义感到不安?按照布鲁贝克的分类,依据现代政治程序建立的法国式共同体及其认同政治并不会引起过多负面情绪,因为随着这一过程的推进,不同的民族身份将逐渐弱化。在此意义上,欧盟正是符合康德式世界主义方向的,但即便如此,近10年来的现实中,民族主义思潮仍不降反增。 诚然,民族主义无论对内抑或对外都常被看作某种危险,但涂尔干和格卡尔普的这一关联恰恰表明,如果任何国家都无法脱离道德生活,那么它也无法摆脱“民族”。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到底来自哪里,又为何这么重要?它是不是重建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需的过渡机制?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审视民族主义所涉及的文化遗产、历史以及地缘政治空间之间的关系,以找出民族主义的真正作用。 诚然,民族主义无论对内抑或对外都常被看作某种危险,但涂尔干和格卡尔普的这一关联恰恰表明,如果任何国家都无法脱离道德生活,那么它也无法摆脱“民族”。所以我们应该反思,令人不安的民族主义到底来自哪里,又为何这么重要?它是不是重建现代国家过程中所必需的过渡机制?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需要重新审视民族主义所涉及的文化遗产、历史以及地缘政治空间之间的关系,以找出民族主义的真正作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