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28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89期在线举行,主题为“从现代国家的建设到商务公司的起源”。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亚光主持,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龙登高评议。

张泰苏老师首先介绍了本项研究的缘起。他始终对18—19世纪亚洲与西欧之间的“大分流”现象的制度解释怀有浓厚兴趣,但这一宏大话题往往需要独特视角切入。在此前的研究中,他从资本积累的视角入手,提出在早期工业化进程中,新兴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一般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西欧和日本等国的工业化进程无不以某种程度的资本集中为前提;中国虽然早已建立了经济腾飞所需要的市场、产权等基本制度,商业文化亦由来已久,但资本积累相对薄弱,从而限制了工业化的推进。
 在早期工业化时期,资本集中并不是以资本市场为主体,而是依托三种基本的制度渠道。第一是土地集中。土地是前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在资本积累中发挥关键作用;土地集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二是税收。历史上的日、德两国就是通过国家税收建立国营经济,进而反哺私营经济,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第三是商业合资。合资形式放松了对资本积累的要求,既不需要国家持有巨额资本,也不需要众多大资本家的存在,只需一些中等规模的投资者即可完成资本积累过程。
在早期工业化时期,资本集中并不是以资本市场为主体,而是依托三种基本的制度渠道。第一是土地集中。土地是前工业化时代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在资本积累中发挥关键作用;土地集中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过程。第二是税收。历史上的日、德两国就是通过国家税收建立国营经济,进而反哺私营经济,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第三是商业合资。合资形式放松了对资本积累的要求,既不需要国家持有巨额资本,也不需要众多大资本家的存在,只需一些中等规模的投资者即可完成资本积累过程。
然而,相比于其他形式的经济合资,商业公司(business corporation)的历史非常短暂,大约在18世纪后才逐渐普及,其经济功能又非常特殊。这引起了张泰苏老师及其合作者的思索:为什么商业公司这一在资本积累史上发挥关键作用的组织兴起如此晚近?要讨论这一问题,首先要对商业公司给予明确定义。目前学界一般公认,商业公司应满足如下六个基本的法律条件:一是独立法律人格,指公司作为独立个体参与经济活动;二是合伙管理体制,指不同投资者对公司进行共同投资并参与管理;三是合资股份制,指投资者根据持有股份享有发言权和投票权;四是股份锁定,指一旦投入就不能轻易撤回;五是资产分割制度,包括有限责任和资产防御两部分,分别保障股东不为企业额外还债、企业不为股东额外还债,从而降低股东之间的合资风险;六是可自由交易的股份,指不需要经过其他股东批准即可交易自己所持股份,这一制度以资产分割制度为基础。
在以上六个法律条件中,前四个条件自古就已存在,最迟不晚于中世纪就普及于欧亚大陆的各大商贸中心,有些在罗马时期就已普及于地中海周边;后两个条件则在近现代才出现,而这二者才是商业公司制度的经济核心,进而极大推动了资本积累的速度。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两个制度出现、普及得如此晚?一个直觉解释是,这两个制度是较为复杂的,前现代时期的经济活动较为简单,人们很难构想出这样复杂的制度。但是事实上,许多前现代经济体中已经存在类似于资产分割的法律制度,如典权、抵押权等,但并未适用于资本合资行为。这推翻了此前的直觉解释,引发了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随后,张泰苏老师阐述了既有文献对上述问题的解释。目前经济学和法律史学者对此的解释大致可分为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类。需求侧着眼于商业公司兴起的经济环境,特别看重长途、跨地域贸易对于资本积累和资本稳定的特殊需求;但这一类解释需要进一步脱离长途贸易的特定历史叙事,使其更适用于现代的社会环境。而供给侧则着眼于国家的自律能力,依据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可靠承诺理论”(credible commitment),认为只有当国家可靠地承诺尊重私有财产时,公司制度才可能得以普及;但这一类解释同样有其漏洞,即忽略了国家建设在现代公司史里所起到的正面作用。

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等于1989年发表《宪政与承诺:17世纪英国公共选择治理制度的演化》一文,提出“可靠承诺理论”。
上述两类既有解释的缺陷明显削弱了其解释能力。以清末民初的中国经济为例,当时中国已出现了大规模的跨地区贸易,同时由于政府过于弱势,也能提供可靠产权承诺,但公司制度并未原发性地出现;即使在1904年,清政府有意引进商业公司制度后,私营部门依然对此反应冷淡,直到1930年后才略有普及,但规模同样非常有限。正是基于已有理论的缺陷,张泰苏老师及其合作者希望在他们的研究中提供更为细致、普适的理论框架,即在需求侧进行抽象化、理论化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供给侧提供新的视角,正视并解释国家能力建设对于公司建设普及的正面推动效果。
接着,张泰苏老师着重从需求侧、供给侧及二者的接洽等方面阐述了其理论框架。从需求侧的视角来看,根据科斯、威廉姆森等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企业的意义在于以立体管理而非平面合同的方式去进行较为复杂的经济合作,而资产分割制度的建立将进一步降低企业合资的风险。但是,这种意义在信息成本较低的熟人合资关系中并不显著;在陌生人之间,也只有当合资关系复杂到一定程度之后,资产分割制度的价值才能真正能显现出来。除了社会关系的生疏远近之外,影响合资行为复杂性的因素还有若干种,包括合资人数的多寡、所进行的经济行为的复杂程度、投资关系、是否属于剩余索取者(residual claimant)等。
而供给侧的论点只有从需求侧入手才能理论自洽。资产防御制度无法通过私人合同自行形成,而是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认可,因为债务的偿还方式不仅取决于债务人,还取决于第三方债权人。那么,什么样的立法单位会有意愿提供这样的制度认可?在前现代社会里,经济制度往往来自以下三类组织:其一是村庄、宗族等熟人社群,其二是商会等跨越熟人社群的私人组织,其三是具有正规化强制力的国家。尽管许多熟人社群都具有在内部制定和推行公司制度的能力,但其需求侧动力显然不足;而商会等跨地域组织的强制力又高度依赖于声誉网络(reputational networks),因而一般只能提供比较基础的合同执行功能,却难以管理复杂的、确定性偏低的经济行为。

山西太谷晋商
前两者的功能局限在公司制度面前被进一步放大。由于股东都是剩余索取者,面临的收益不确定性很高,公司的运行极度依赖于其合资协议与管理规章的公正、统一执行,这很难通过非正规化的人际网络实现。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声誉网络依赖于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否,因此很难在大量陌生人之间保持足够的公正性和统一性。综上所述,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撑,陌生人社会的复杂执法能力将很难提高,也就无法支撑不确定性较高的经济行为。
相比于民间的声誉网络,国家的供给侧功能独特而不可替代。不过,这种理想状态也需要相当大的政治、财务与行政投资方能实现。更重要的是,国家可以通过制度的正规化保障执法的统一性,从而致力于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可靠承诺”的题中之意,但与已有理论相比,却格外凸显了国家在商业公司制度建设中的积极意义。上述理论框架的基本结论是,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先于国家建设而在民间自行普及的商业公司制度。
不过,要严格证明这一结论,还需要详细考证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史与经济法史。张泰苏老师提供了一个较为典型的例证,即中国的近现代公司制度史。学界一般认为,1904年之前,晚清社会并不存在真正的公司制度,民间的合资企业一般以家族为枢纽,没有完整的资产分割制度,尤其没有资产防御机制。但是在这一历史阶段,跨地区、跨社群的经济行为已经存在,并确实产生了对资产分割制度的社会需求,故而资产分割制度的缺失也阻碍了长距离、大规模的商贸发展。此后,清政府立法建立公司制度,但民间支持者寥寥;1930年后,随着国家司法能力的增强,私营公司数量开始显著上升;直到改革开放后,私营公司真正成为主流的市场主体。

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1799)
而在欧洲、西亚和美国的公司法发展史上,公司的推广与国家能力的提高也是明显同步的。以英、美、奥斯曼帝国为例,在现代国家真正出现之前,能够运用资产分割制度的经济体几乎全部是由国家直接投资或管理的,如东印度公司等。目前,张泰苏老师及其合作者并未发现历史上存在反例,但亦不能排除反例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本项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推导层面,在实证层面上则主要提供的是假说而非结论。
评议环节
评议环节,龙登高老师高度肯定了此项研究的整体思路和拓展价值。他指出,张泰苏老师从商业公司的原生形态,即西欧大航海时代的特许经营机构入手,提出了理论假说,同时考察了中国等后发国家对公司制度的移植和模仿过程,并探讨了后者发展不尽如人意的原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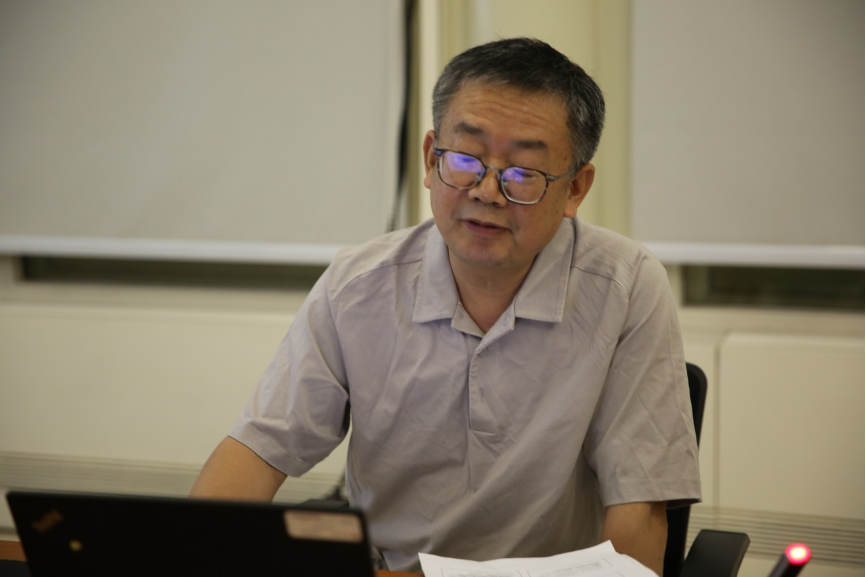 龙登高老师认为,原生形态的商业公司,是一个从萌生、形成到成熟的演化过程。荷兰与英国在16世纪后期最初基于一次性的熟人合作项目,17世纪发展为永久性的公司组织。在此过程中,由于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与权力制衡体系的发展,国家的可置信承诺得到强化,推动了资产分割制度的演进,进而促成了新的商业公司走向成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更强调国家授予特许经营权与需求推动对商业公司兴起的影响,而张泰苏老师的研究则指明了国家能力提高与商业公司起源之间的关系,拓展了研究视野。这也启示人们,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将释放能量,无论是历史上的特许公司还是当今的国有企业,无论是官员贪腐还是信用背书。
龙登高老师认为,原生形态的商业公司,是一个从萌生、形成到成熟的演化过程。荷兰与英国在16世纪后期最初基于一次性的熟人合作项目,17世纪发展为永久性的公司组织。在此过程中,由于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与权力制衡体系的发展,国家的可置信承诺得到强化,推动了资产分割制度的演进,进而促成了新的商业公司走向成熟。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大多更强调国家授予特许经营权与需求推动对商业公司兴起的影响,而张泰苏老师的研究则指明了国家能力提高与商业公司起源之间的关系,拓展了研究视野。这也启示人们,政府与市场的结合将释放能量,无论是历史上的特许公司还是当今的国有企业,无论是官员贪腐还是信用背书。
互动环节,张泰苏老师与龙登高老师及现场听众就清末租界的治理特色、长子继承制对资本积累的影响、剩余索取权与不完全契约的关系、儒家思想与资本主义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他表示,诚如龙登高老师所说,无论是原生形态还是学习模仿的商业公司,都经历了渐进发展的过程。早在大航海时代早期,欧洲地中海沿岸的城邦交易中就已出现了一次性的商业合资行为,但当时人们对资产分割制度仍有很强的不信任感,认为其制度成本较高,难以保证长期性收益。而在1920年前后,中国虽已引进公司制度,但仅有百余家商业公司建立,且绝大多数位于上海、江浙一带;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注册的商业公司近1000家,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与改革开放后的爆发式增长不可相提并论。这进一步印证了国家能力在商业公司建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