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5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支持的“未名学者讲座”第9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城市史的书写方式——多维度的生活方式与交织的智识传统”。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研究员许立言主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昝涛主持,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唐晓峰和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评议。

讲座伊始,许立言老师指出,本次讲座将从副标题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切入,探索城市史叙事的新可能。讨论城市史必须先了解城市。城市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物,当今超过一半的世界人口是城市居民。许立言老师以古今中外的城市案例说明,虽然身处全球化的时代,城市依然在诸多面向上保留着异质性:物质形态多样、规模大小不一、人口多寡不等、经济结构各异、存续时间有差……正是因为城市是一个有着复杂面向的实体,所以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城市,进而有了书写城市史的不同进路。
一般而言,城市史的书写方式有三类。“正统”的城市史是城市建筑史,诸如《世界城市史》等经典教科书均侧重于书写城市的物质空间。近些年来涌现出的一批城市史研究则注目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关注城市的社会与文化层面。第三类则是走以史代论的路径,通过书写城市史来建构城市(规划)理论,阐发应该建设什么样的城市这一理论思考。此外,环境史等其他领域的专门史也会或多或少涉及与城市的纠葛。统而言之,许立言老师认为,在现有的关于城市史的叙事中,至少在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个方面存在值得探究的分歧。
一
本体论方面的问题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具备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认识论方面的问题是,如果城市研究是希望获得关于城市的知识,那应该秉持怎样的信念去获取这一知识?
就本体论问题而言,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什么是城市有着各异的回答。考古学者戈登·柴尔德基于田野工作的经验,很大程度上从文明的构成要素出发,总结出构成城市的十个条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从中世纪晚期德意志地区的案例出发,围绕规模、密度、经济结构和心理文化等方面给出了城市的操作化定义。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则相当诗化地对给出了城市的定义:“城市是圣地,城市是容器,城市是融合,城市是要塞。”城市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以综述的形式概述了地理学、历史学、统计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各自是从什么角度来看城市的,如此便提供了定量研究的思路。理查德·杜威在1960年发表的文章便收集了18个作者描述城市时用的40个关键词,考察城市的定义。

▴
柴尔德在苏格兰斯卡拉布雷新石器时代遗址
在上述观念性的定义外,联合国统计局以述而不作的态度,收集汇总了世界各国在城市人口统计工作上的操作性定义,这使我们可以了解各国以何种指标定义城市。各国的操作性方案既包括行政区划、人口规模和密度、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等客观指标,也包含诸如“社区感(sense of community)”等社会文化和心理层面的指标。许立言老师认为,尽管几乎没有哪两个国家对城市有着相同的定义,但是综合上述观念性和操作性的标准,可以就城市归纳出6个维度和特征,即政治文化、建成环境、人口统计、经济产业、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基于此,可以认为城市概念的内涵(即包含的维度)是普遍的,外延(即各维度的具体表征)则因历史地理语境不同而变动不居。但在本质上,正如沃斯的名言,城市是一种区别于农村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具备哪些特征,城市就包含了哪些维度。
从这一本体论出发,讲座接着考察了城市研究的认识论问题。许立言老师指出,在城市研究的认识论问题上向来缺少共识。城市究竟是应然还是实然(标识着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的分野)、是现象还是实证(决定了应该用阐释还是解释的方法)、是确定性的事物还是从复杂系统中涌现出来的不确定的现象(即还原论和复杂系统论之争)……关于城市研究应该秉持何种信念存在许多分歧,不同学科有着其特定的智识传统。
在建筑学传统方面,建筑师们自古以来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亦利用物质空间来表达社会秩序和宇宙观。例如,在早期城市中可以发现“圣界”和“凡界”在空间上的区隔;克里夫兰城在城市美化运动中将购物中心置于市中心,反映出当时被资本主义塑造的时代精神;现代主义的建筑师则较其早期同行而言更具自我表达的意味。与建筑学相匹配的是工程学传统,其代表是20世纪的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其城市建设在统一的计划经济框架下完全变成了数学优化问题。在这一传统中,城市研究与价值完全解绑,因为如果说工程学传统关涉价值的话,也仅仅是最优化的价值而已。

▴
莫斯科圆形房屋,1972年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西方自然主义、人权思想的兴起,景观-生态学的传统融入了城市研究的范式之中。城市隔绝了人与自然,让人们产生了“分离焦虑”,所以人们会希望在城市里引入自然、发现自然。地理学传统则发生了从与价值无涉的工具地理学(如19世纪的区位论)到20世纪人文地理学的转向,更为关注人地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在特定空间的互动。与此同时,社会学传统也汇入了城市研究的脉络中,强调城市社会是不同于农村的社会,这一点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而不断凸显。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共享一块土地,相应的规制则渐渐兴起。在更加实践性的面向上,从19世纪中期开始,以各类市政立法为标志,政法传统也加入进来。此外,还存在着几乎与建筑学传统一样悠久的知识传承,即自城市诞生以来,人们一直在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城市、是否存在一个理想的城市,这就是乌托邦传统。

▴
《真理之城》(1609)
二
在回顾了城市的本体论与认识论面向后,许立言老师提出了一种新的叙事线索:将城市作为一个生活方式的多个维度,和城市研究作为一个智识传统的多个视角结合起来,重新构造城市史的叙事,以实践和思想两个层面共同勾勒城市的脉络。
10000BCE-2000BCE,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到欧亚大陆的各个区域,出现了大型的人类聚落、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也即发生了考古学意义上的城市革命。在此时期,以戈登·柴尔德为代表的考古学者,几乎将文明与城市等同起来。接下来的古典时代(2000BCE-400CE),中国和西方都出现了最经典的城市,出现了“虚伪游手”等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有大量的技术创新,如二里头遗址的木构技术、环地中海文化圈的希腊柱式、古罗马城的拱券与穹顶。此时,人们也形成了对营造城市的最初的思考。在中国,西周初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城市规划活动——召公卜洛,《周礼·考工记》中给出了一个儒家的理想城市模式:“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法家的《管子》则针锋相对地认为“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中山国墓葬发掘出的《兆域图》则表明人们已按照设计平面图来施工建设。在西方,伯利克里时代的建筑师希波丹姆提出了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城市方格网系统,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盛赞——通过城市规划的方式,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却对公民社会作出了贡献。与奥古斯都同时代的建筑师维特鲁威,则将希腊-罗马的建筑传统记载下来,写成《建筑十书》,确定了建筑的三大原则:实用、坚固、美观。

▴
世界上最早的铜板建筑规划图——错金银铜板兆域图
1978年出土于河北平山三汲乡战国中山国王墓葬
在中古时代(400CE-1400CE),中国的城建依然繁荣但创新略显乏力,里坊制在唐长安城达到了巅峰,而里坊制崩坏后,宋汴梁城出现了如《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现代最为熟悉的城市生活面貌。元明清三朝营建的北京城则大抵沿革至今。在国外,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城以其圆形的城市形态独树一帜,代表着中东传统的一个侧面。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则依托城堡和教堂逐渐发展起来。欧洲中世纪的晚期的城市出现了韦伯所谓的“世俗的回归”,城市得到了再发现。在思想层面,中国很早已经有了发达的地图学(如“制图六体”);北宋时期的《营造法式》作为竣工验收手册标定了建筑规范,标志着古典建筑学的成熟。当然,人们也从未停止思考人类的聚居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如《桃花源记》和《上帝之城》等作品即是其中的代表。

▴
圣母百花大教堂
在文艺复兴与近代早期(1400CE-1800CE),城市在实践上开始复兴,如圣母百花大教堂是对古罗马大穹顶技术的复兴和再创造,格网形制再次出现,人们再次探索理想的城市方案,到了18世纪则出现了巴洛克的壮丽风格。此时,人类关于城市的思想也开始活跃起来。新一代的建筑师构想各种各样的城市,尤其是到了17世纪诺利画出了罗马地图,这是第一幅被建筑学称为“图底关系”的空间图示,在建筑学看来非常现代,因为其在强调空间而非建筑。与此同时,人们关于理想城市的思考极大丰富,达芬奇从健康城市生活的角度设计了理想城市方案,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者也想象出乌托邦、新大西岛、太阳城、基督城等综合的理想社会。
到了工业革命时代,一直到现代性的生发(1800CE-1960CE),人们在城市的实践和思想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工业城市取代中世纪的城市而兴起,资本主义支配了城市空间,出现现代格网和城市功能分区。为了预防革命,统治者打着城市美化的幌子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改造。随着人们与自然的分离焦虑,城市出现了公园。城市新基础设施(下水道、地铁等)在此时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相应的,人们的思想空前地活跃起来,(工具)地理学的传统、自然-生态的传统、政法传统的规制、社会学的传统纷纷兴起并影响城市。到了20世纪初,随着现代主义建筑运动,涌现出了关于城市的新的想象,如赖特的“广亩城市”和柯布西耶的“光明城”等。随着现代主义建筑师们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城市规划史上的第一个综合纲领——《雅典宪章》,其主导了战后城市更新和大都市区/城市群的建设,推动了西方第一轮城市化的完成。在这一时期,人们同样没有放弃对理想城市的思考,既有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探索,也有对百年工业革命城市的反思,更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验。

▴
赖特“广亩城市”模型
当前的时代,许立言老师援引地质学的流行观点,称之为人类世(1945CE至今),这既是基于地质历史分期中对人类因掌握核能而产生了真实的地层影响这一事件的考量,也反映了城市历史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折。虽然现代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新首都营建中尚有用武之地,但西方世界的城市尤其是老城已然出现了逆城市化和城市危机。与此同时,在思想界,随着民权的普及和环境运动,人们开始思考诸如“社区感”等让柯布西耶等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忽略的观念,也以社区反抗运动影响着城建的实践。空间政治、人文地理学、景观生态分析、社会学的传统等等思潮不断汇聚,导致了第二个纲领性著作,即《马丘比丘宪章》的诞生。这一宪章强调人与人的连接,城市规划便重新转向人性。但与其说这个宪章是新的综合,不如说是一个分歧的起点。19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政治日渐被身份政治所支配,关于身份政治的城市实践已经破碎至极,以至于无法分辨城市智识传统的主线何在。
基于上述的讨论,许立言老师给出了自新石器晚期城市革命以来至今乃至未来的城市史断代、分期与时代主题,展示了讲座开头提出的一种新的城市史书写方式。
三
在讲座的最后一部分,许立言老师对城市史的书写做了展望。综观关于城市史的书写方式,以《雅典宪章》和《马丘比丘宪章》为代表的两次伟大综合及其之后的分歧,向未来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关于城市规划的知识究竟是走向新的综合,还是会继续开枝散叶使我们抓不住一个主流?以身份政治的支配地位来看,当前已经出现了无限细分的趋向,再难有综合一说。与这一表面繁荣但实质沉寂的智识活动相伴的,是完全趋同的城市格局和平庸的城市景观。那么,关于城市的智识传统是否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来结尾?许立言老师认为,当前的情况离令人满意尚有很大的距离,城市研究中尚有许多复杂问题有待解答。
例如,现今的城市规划智识传统,不管其如何普适,都依然是西方的传统,对于第三世界来说,哪些是世界的哪些是民族的这一问题有待回应。又例如,城市研究的主要学者们在2020年发表了一篇备忘录,列举了二十余条要关注的问题,号召建立新的城市科学,但其反复强调的“深植于历史中的城市研究”又引发了新的问题:我们追求的城市知识到底是关于历史的阐释性叙事,还是普适的(社会)物理规律?在城市的想象方面,人们曾经有勇气去想象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存在,但现在我们似乎丧失了这种勇气,这一境况亟待改善。
最后,许立言老师再次援引路易斯·沃斯的名言作结: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城市的知识,就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为何得以存在以及将要如何存在的知识。我们有义务去接着书写城市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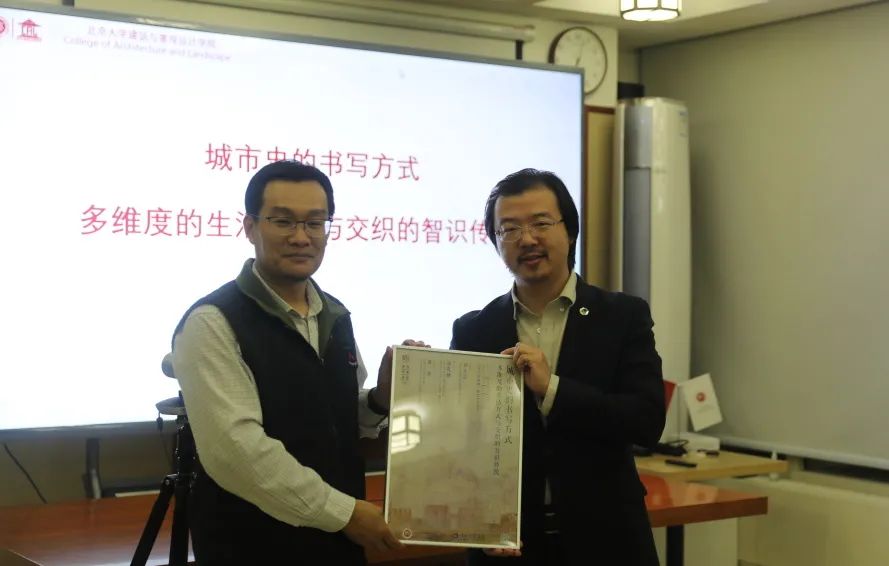
▴
昝涛老师为许立言老师颁发未名学者证书
评议阶段,唐克扬老师首先指出,城市尺度决定的问题复杂性叠加学科专业化的影响,使城市研究需要克服相当大的困难。城市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也是社会生活本身的一个部分,必然会包含行动的传统。许立言老师在梳理了不同的学科传统之外,还点出了诸如政法传统和乌托邦传统等内容,是难能可贵的。其次,讲座用智识传统而非知识传统为切入点,提示我们在关于城市是什么的理解中孕育着知识发生学的问题,城市史研究不是在积累无穷无尽的经验,而是揭示智识传统对特定经验的反映。交织的智识传统应该是一个行动纲领,将多维的生活方式资料编织起来,使其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最后,在研究的基础上,要以知行合一的姿态,在续写城市史的意义上,将关于城市是什么的思考贯彻到城市规划中去。
唐晓峰老师谈了三点体会。一是许立言老师在梳理各学科的智识传统时加入了时间的维度,理清了每个学科在何种背景和特定节点下进入城市研究,更为细致地描绘了城市史研究的脉络。二是将实践和思想这二者结合,以新的叙事方式构建了城市思想史,关注每一个历史阶段被特别追求的本质,触及了问题的历史性意涵,是一个很好的叙事。三是“人类世”的概念,点出了现代化过程中城市系统的扩散与农村系统的萎缩,城市相对而言已不再是独特的存在,这对我们理解新的时代下的城市有很大裨益。
问答环节,许立言老师对现场听众所提出的城乡对照研究、从智识传统出发理解城市的路径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