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3日晚上,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第117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哄唬’与‘礼节’:变革中的中人、生活形式与合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林叶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评议。

本场讲座的内容来自林叶老师博士研究期间的田野调查,主题关于基层动迁者如何与被动迁家庭谈判,以及探讨这样的材料对于政治人类学有何种意义。林叶老师从一张田野调查中的现场照片入手,指出中国货币化征迁的表面特点是谈判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需要计算的事项,而这背后的实质意涵则是:家庭政治在这场货币化征迁过程中与公共政治发生的关系。
此前学界和媒体的主要叙事,是认为被动迁家庭的家庭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被公共政治所牵制和左右。林叶老师则强调相反的过程,即家庭政治反而渗透了征迁的公共政治,使其被家庭伦理化。第一个体现是基层动迁者不仅被卷入家庭政治,而且其谈判工作正是通过、也只有通过与被动迁家庭的伦理生活相关联、主动进入甚至介入到伦常性的“家务事”中,才能真正得到开展。第二,所谓“货币化”的计算方式,不是“市场化”而是“伦理化”地进行着,货币化补偿的每一笔账都有着关乎“家庭内公正”的意味。
首先,林叶老师详细讲述了征迁过程中的多个层级和主体。她尤其关注基层“拆子”即征迁现场的小组组长和小组组员,他们是被动迁家庭长期、实质面对面的征迁力量代表,不仅在动迁队伍中占比最大,工作内容也最重要。她分析认为,在当地方言中,“X子”首先主要被用为对具有某种专长的平民群体的称呼,例如厨子、戏子。其次,这种称呼带有贬义,有的情况下主要指身份低贱,比如厨子和厨师相比,戏子和演员相比,都是对从业人员更为贬损的叫法;有的情况下则指向人格缺陷或有问题的、失败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如混子、喷子、痞子。当“拆子”被作为一线征迁工作者的自称时,既带有对自己所具备的专业技艺的自信,又带有一种独特的对自己人生“失败感”的强调。此外,“老拆子”一词,不仅指完全把握专业的征迁知识,而且“吃透了政策”,更指具有高明的谈判技艺和化解问题的门道。

▴
征迁现场的权力结构
接下来,林叶老师讲述了在不同的时期,动迁过程中的人们以什么样的状态进行生活和互动。其中,在以地补路政策带动的最初的抽调实践之后,城市房屋征迁的货币化改革和大规模城市棚户改造项目的涌现催生了针对区县内干部和没有编制的政府基层工作人员的大规模抽调;后者在动迁谈判中展现的实际工作能力,使其在动迁现场的地位逐渐上升,并进而构成基层征迁小组的主流,他们与干部之间的层级区分也逐渐模糊。而在政治震荡之后,随着超级动迁项目的停滞,这些干部和非编制人员成为了原单位“回不去的人”,进入到一种长期停留并生活在征迁工作现场的度日和栖留状态,以零碎而反复的节奏渐次累积起与被动迁家庭的谈判。林叶老师提醒,这类谈判中,包括纠纷、矛盾在内的问题和困境是非系统性地出现的,这就使得一方面被动迁家户不停地而又无规律地产生造访小组的需求,另一方面小组人员时刻面临变故和新的局势,这种特点令小组无法主动把握而只能总是处在准备迎接新事件的状态中。
作为迂回于项目领导者与被动迁家庭之间的“中人”,拆子通过照管的权力和机会进入家庭政治。作为照管者,拆子首先是“管理补助”之人。货币化征迁不完全是市场化,“数人头”和“托底”等有平均主义意味的社会福利照管意图仍然在延续。定额补助(低保补助、大病补助、残疾补助、高龄补助、困难补助)对应着社会福利意义上的特殊身份:低保户、大病患者、残疾人、高龄老人、特殊困难户等,这些都指向被动迁家户非常具体的生活实际。对此,拆子会尝试“摸底”每家每户所谓“花边的东西”和家里的变故,在此过程中他们的人品也受到被动迁者的实质关注。同时,“抽调制”下的“动迁队伍”本身就是通过动员本地政治结构中人(而非拆迁公司)来进行土地经营(官-民关系)的结果,加之后期加入的众多外聘人员往往与其来自动迁队伍的介绍人之间具有信任-担保的社会网络关系,这使得这个群体中逐渐长养出特殊的工作伦理,尤其是基层小组中的外聘人员追求尽量把纠纷化解在自己的层级,不给位于征迁力量更高层级的担保人即关系的来源人添麻烦。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林叶老师结合田野经历分享了三个个案,从她在征迁小组中的观察出发,生动地讲述了拆子为什么需要以及如何介入到被动迁家庭伦常性的家务事中,如何通过他们自称的“哄唬诈骗”实现礼、守住节。其中,莫振案的问题是拆子是否应以“公”的身份解决家庭矛盾:小组和指挥部具有“公”的形象,被被动迁者想象为家庭矛盾的化解途径。但实际上,小组一方面主动将儿子的变卦告知父亲,却拒绝进一步以公的身份介入以回应家庭矛盾,而最终将解决的事务推回到家庭内部。而在万金生案中,看似不合规的6万补助实际上十分精确地朝向着万家未来的“分家安排”。波老四案则在通过“骗”的手段实现正当的“礼”的同时,用“节”保住了骗的底线,即不违背继承法平均主义,但隐瞒本地优惠政策。
这些个案有很强的普遍性和理论意义。“有礼有节”指向拆子们的“为人之道”,它并不一定带来高效率,但关乎基层拆子社会的“自尊”,而从前以捞外快为临时动力的“抽调大军”逐渐成为一个握有成熟而公认的工作伦理的、有度日心态的“平民专家队伍”,是这种“自尊”的前提。正因为掌管补助,拆子得以更深入地介入家庭矛盾;虽然这类在拆迁款之外的补助并不是直接针对家庭矛盾的补助,但事实上常常被用于解决家内问题。城市征迁补偿带有的社会福利再分配色彩由此成为一个具实、明确并且可以被言说出来的问题,使家庭矛盾能被“拉到谈判的台面上”。换言之,尽管家庭矛盾本身并不是制度性的社会福利政策所照顾的对象,但补偿安置政策对社会福利的考量推动的潜在认定是,既然“政府在拆房子的时候要管低保、大病、残疾、高龄这些困难,那么征迁中的家庭矛盾也不能不管”。因此被动迁家庭总是主动期待甚至要求动迁小组帮助“摆平”家庭矛盾,而小组人员也在事实上认可并主动“揽起”对被动迁家庭矛盾的处置。
最后,林叶老师讲述了对拆子的观察在“中人”之义上对政治人类学可能的意义。例如,她尝试与格尔茨和Lawrence Rosen对法律实践中事实-价值问题的讨论进行对话。格尔茨对比西方和其他文明中法官寻求正义过程的差别,发现西方法庭上被认可的法律事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执行法律的真实含义是对事实构成和规范进行的配对。Rosen则提示例如伊斯兰社会的法官卡迪,其所依循的不仅是特定的教法规范,也包含当事人在案件中和庭审中的实际行动,或言生活形式。又如,她认为拆子与被动迁家庭的关系与Ifugao社会中的monkalun共同提示的是,“中人”并不一定是“甲方-中人-乙方”框架中的中间者,而也可能是甲方与乙方的交集部分,类如“两方共同的'纵兄弟’”,保持着和两方一种不太近也不太远的亲属关系,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彻底解决纠纷,而在于总是出现并嵌入在纠纷的路途中。再如,她认为拆子掌管补助的自由裁量权(Discretion)亦不同于常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中的“权”,而是一种自行决定权,是情境“逼发”的主动行动。最后,她认为拆子作为中人之义,提示着一种另类的“合作”,也即“冲突”并不必然为“恶”,而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积极的社会交往。于是,如果重新审视这场因城市建设而掀起的、主要显现为冲突形式的、既近且久的对峙,也会发现,它的其中一部分恰是一种“良性”的合作,提供着对以“冲突—合作”为二分的政治人类学传统预设的省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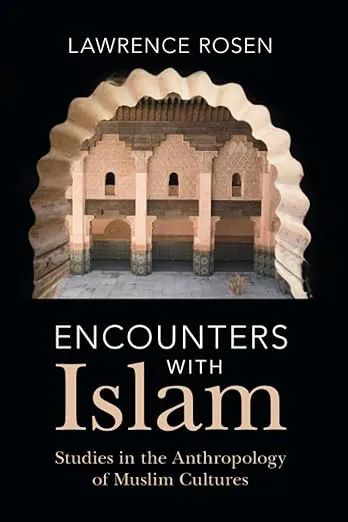
▴
Lawrence Rosen, Encounters with Isl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
交流环节
朱晓阳老师赞扬这是一场信息量很大的讲座,将拆子和被动迁家庭之间的互动展现得鲜活而有趣。在林叶老师的田野地,“拆子”和“钉子”形成了相依为命的共同体,有生动的时间、空间和过程,而且是在一个守规矩、讲和平的规范框架内。朱老师认为,拆子的民族志不是格尔茨的框架可以解决的,不是地方知识而是“地方世界”,西方学者认为不同文化所处的世界是一样的,只是表征不一样,但拆子的实质理性不止是一套话术和表演,是将心比心、大家都要过日子的原则。这是一个实在的社会关系而并非表征,构成了这些“中人”的处世原则。他们不规范的行为虽然只是个案,但是地方特有的法,和现代司法不一样,甚至都没有规范的科层制,但也有独特的范式和逻辑。例如朱老师所关心的“地势政治”,“地势”在现代法律中是找不到的,但在中国是一种实在,也是政治生活中的实在。基层的政治实践者(包括村民/业主、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对地势问题非常重视,相反,社会科学界更多是从政治、经济等视角去看待城市化中的诸多问题。作为研究者,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将这些问题从隐蔽的地方凸显出来。

▴
朱晓阳老师为林叶老师颁发未名学者讲座聘书
讲座最后,林叶老师对朱老师的评议进行了回应,与会学者与听众就地方政府征迁、家庭政治与公共政治伦理化、政治人类学传统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