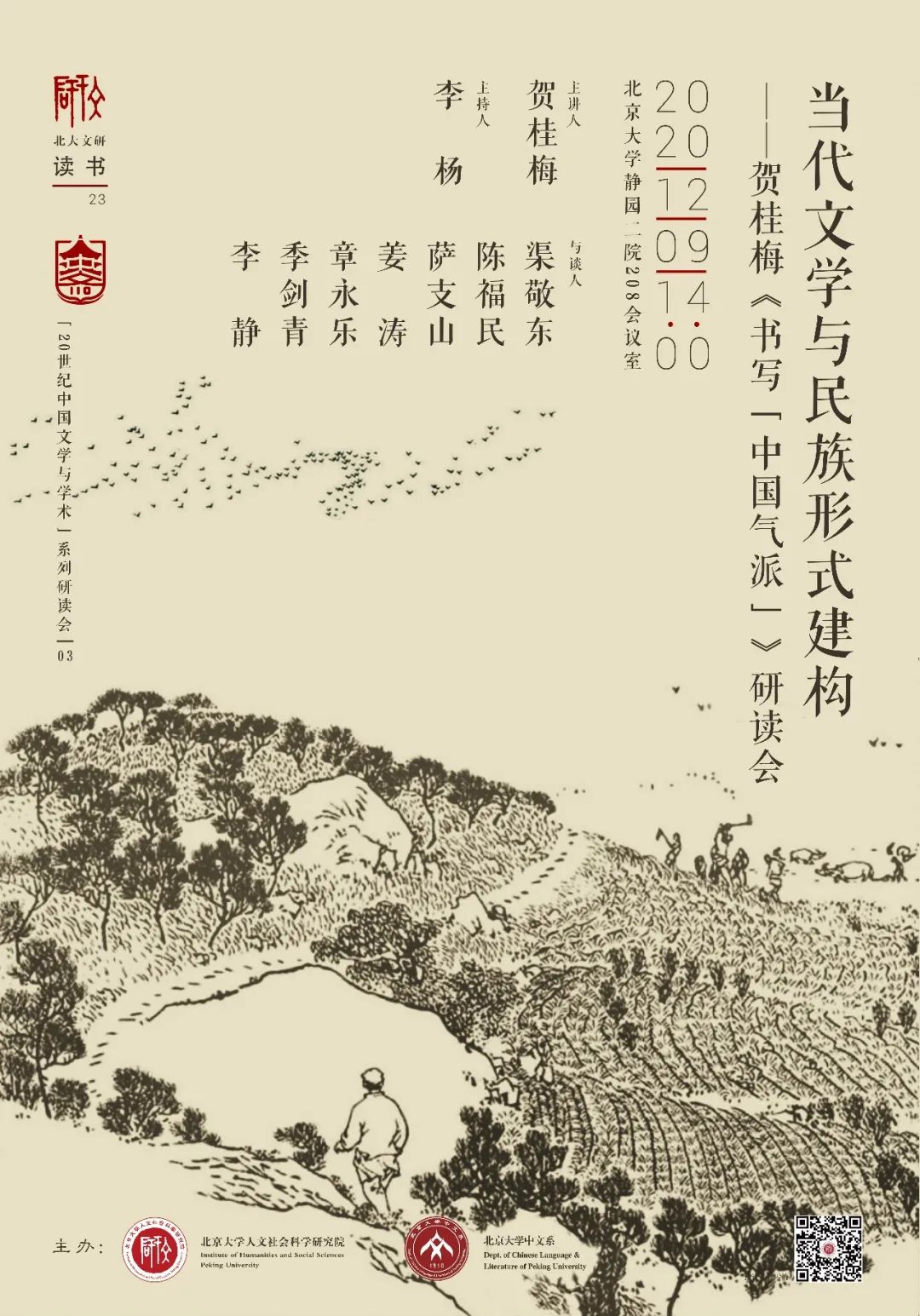
文研读书|第23期
2020年12月9日下午,“20世纪中国文学与学术”系列研读会、“北大文研读书”第二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研读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单位的多位学者与会。本次研读会由文研院、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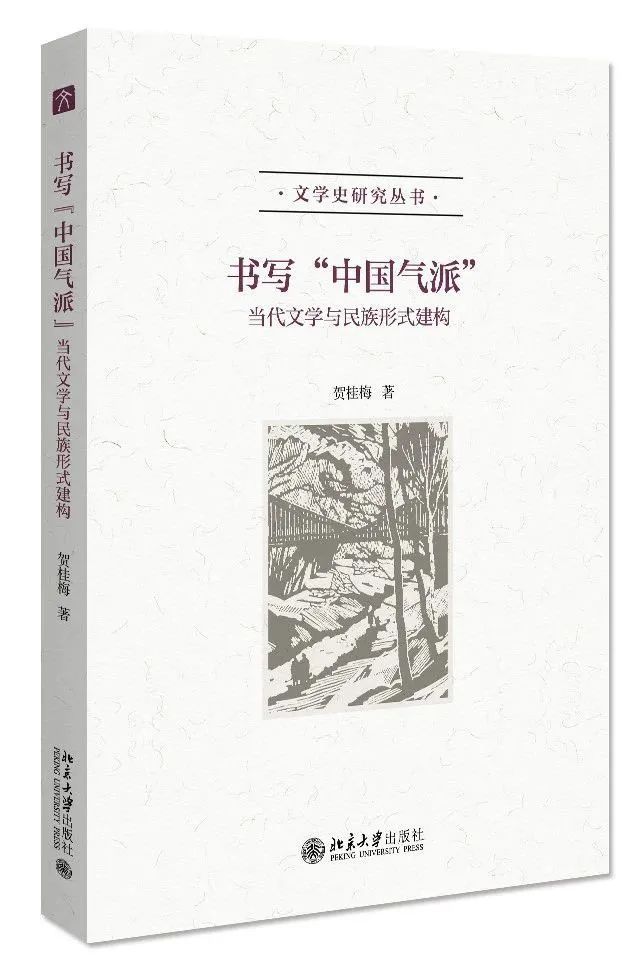 研读会围绕贺桂梅教授新近出版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展开。在既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当代”是被较多讨论的对象。而对于“中国”意涵的关注,则始终不足。“当代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产物,“中国性”是其基本品质与核心特征。1940—1970年代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的理论探讨与文学实践,为打开“当代文学”的历史视野提供了重要参照。《书写“中国气派”》即循此系统考察了赵树理、梁斌、周立波、柳青等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以及革命通俗小说与毛泽东诗词两大特殊文类,推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的总结与“当代文学”的理论重构。此书历史性地分析了制约着1940—1970年代中国及其文学实践的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民族主体性建构的不同面向,强调当代中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独特性及其文学实践的复杂层面。这对于摆脱主观性的价值判断,而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结构关系中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史,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联系到当前知识界对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问题的讨论,更具有特殊意义。
研读会围绕贺桂梅教授新近出版的《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展开。在既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与“当代”是被较多讨论的对象。而对于“中国”意涵的关注,则始终不足。“当代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产物,“中国性”是其基本品质与核心特征。1940—1970年代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的理论探讨与文学实践,为打开“当代文学”的历史视野提供了重要参照。《书写“中国气派”》即循此系统考察了赵树理、梁斌、周立波、柳青等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以及革命通俗小说与毛泽东诗词两大特殊文类,推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的总结与“当代文学”的理论重构。此书历史性地分析了制约着1940—1970年代中国及其文学实践的现代化、社会主义革命、民族主体性建构的不同面向,强调当代中国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独特性及其文学实践的复杂层面。这对于摆脱主观性的价值判断,而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结构关系中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的实践史,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联系到当前知识界对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等问题的讨论,更具有特殊意义。
研读会伊始,贺桂梅教授首先做主题演讲为新书导读。她讲述自己写作此书的过程、基本设想以及思考和回应的问题。此书的写作主要是探讨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的民族认同问题,以经典作家和作品为核心讨论民族形式的不同侧面,并尝试对新中国前三十年文学进行重新叙述和建构。
 这本书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思考和写作。首先是为什么研究1940—19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贺桂梅教授回顾了1990年代思想界、文学界遭遇的问题,认为自己研究的原点性问题即生发于此,并以系列的研究一直在推进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她以作为现代性例外的前三十年文学为借鉴,跳出“五四”现代性话语和缺乏解释力的革命史话语,从长时段的中国文明史视野探寻西欧现代性之外的思想资源,应对当下遭遇的现代性思想危机。其次是为什么从民族形式问题入手?194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在每个阶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正是当代中国的认同机制保证了当代文学的连续性。从“中国”来思考当代文学,将民族形式扩展为普遍性概念,探讨其如何塑造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也就打开了当代文学研究中被忽视的“中国”概念。最后是采取什么方法研究1940—1970年代的文学?贺桂梅教授在“重写文学史”、传统革命史、“再解读”、“社会史视野”之外,尝试以新的理论方法打开文学,同时又回归文学,对经典文本重新阐释。她希望在三个方向拓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开放的全球史视野、长时段的中国文明史视野以及最为关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哲学。
这本书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思考和写作。首先是为什么研究1940—197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贺桂梅教授回顾了1990年代思想界、文学界遭遇的问题,认为自己研究的原点性问题即生发于此,并以系列的研究一直在推进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她以作为现代性例外的前三十年文学为借鉴,跳出“五四”现代性话语和缺乏解释力的革命史话语,从长时段的中国文明史视野探寻西欧现代性之外的思想资源,应对当下遭遇的现代性思想危机。其次是为什么从民族形式问题入手?1940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在每个阶段都发生了很多变化,正是当代中国的认同机制保证了当代文学的连续性。从“中国”来思考当代文学,将民族形式扩展为普遍性概念,探讨其如何塑造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内涵,也就打开了当代文学研究中被忽视的“中国”概念。最后是采取什么方法研究1940—1970年代的文学?贺桂梅教授在“重写文学史”、传统革命史、“再解读”、“社会史视野”之外,尝试以新的理论方法打开文学,同时又回归文学,对经典文本重新阐释。她希望在三个方向拓展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思考:开放的全球史视野、长时段的中国文明史视野以及最为关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实践哲学。
接下来,各位与会学者先后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认为,此书重新打开了民族形式长期被遮蔽的政治学、政治哲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的维度,这实际上是正本清源。同时,这种解读依然是用文学将其打开,聚焦于文学作品,努力把内在的张力呈现出来,探讨民族形式在文学作品里面如何表现,他认为这一点是此书贡献最大的一个地方。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认为,此书重新打开了民族形式长期被遮蔽的政治学、政治哲学、社会学甚至法学的维度,这实际上是正本清源。同时,这种解读依然是用文学将其打开,聚焦于文学作品,努力把内在的张力呈现出来,探讨民族形式在文学作品里面如何表现,他认为这一点是此书贡献最大的一个地方。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强调,在中国整体的文明传统和近现代的视野中,以“拉长”的方式看当代中国的前三十年。他以贺著中涉及的山水部分为例,在中国文明的三段之中讨论山水之变,即上古的山川祭祀到中古的士人山水再到近现代的山河政治。他认为在这种“拉长了看”的视野中才能理解构成现实实践的要素或根基在哪里。新中国前三十年正是将“大地政治”做到极致的时期,这也与晚清以来中国融入西方的现代系统有关。贺桂梅的新书构建了通过经典作家理解“大地政治”问题的途径,具体则包括探讨涉及的村庄、土地、风景、方言等方面。最后,他也并不讳言“大地政治”的问题所在,即把原来的“天”和“人”转化为“大地”问题。因此,以“大地”作为文明基本构造的同时,我们可能也需要把其他文明传统重新解救过来,在新的时代进行组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认为,此书通过将以往主流文学史书写中相对边缘的概念“打捞”出来,与主流文学史叙述形成了强烈而具有深度的对话关系。此书探寻、回应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包括中国现代性表述盲区中的中国问题、单调的二元论结构问题。新中国前三十年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处于一种无名状态,而此书“打捞”并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问题。文学史书写中历史与审美的二元对抗带来了文学价值认同的高度纯文学化倾向,而这种纯文学倾向究竟是对社会历史的负责还是逃离也值得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福民认为,此书通过将以往主流文学史书写中相对边缘的概念“打捞”出来,与主流文学史叙述形成了强烈而具有深度的对话关系。此书探寻、回应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包括中国现代性表述盲区中的中国问题、单调的二元论结构问题。新中国前三十年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处于一种无名状态,而此书“打捞”并呈现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中国形象和中国问题。文学史书写中历史与审美的二元对抗带来了文学价值认同的高度纯文学化倾向,而这种纯文学倾向究竟是对社会历史的负责还是逃离也值得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萨支山表示,他最欣赏的是此书整体性、总体性的理论视野以及自觉历史化的研究方法。他认为,作者特别敏锐地从民族形式、中国性这一概念对三个三十年进行统合,具有很强的阐释力和概括力,也富于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寻找民族形式,最根本的其实就是构建人民的问题,而民族形式的建构也是此后中国革命最内在、最具核心性的东西。作者的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研究者作为阐释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试图达成互为主体、互为对象的状态,具有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背景,不过这也是一种富于难题性的方法。此书的写作是带着对革命的情感与体认进入1940—1970年代的文学,将这种情感贯注其中,并以此为枢纽,往上走到现代文学,往下走到新时期文学,因此才有可能以某种整体性的方式呈现三个三十年,而这正是最让人感动也最有力量的地方。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看来,此书将民族形式问题从现当代文学学科内部文学思潮或理论史层面的讨论提升到非常高的层次,指向了1940—1970年代的人民国家的建构,突破了学科限制以及支撑学科的单一民族国家制度的理解方式,具有全球的文明史和世界史视野。作者将民族形式以及民族形式背后的人民—国家这种政治作为研究当代文学的一个贯通性视角,勾连现代中国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他也提出了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具体问题,包括有些论述打开、提升的过程稍微有些明快。例如书中借用的柄谷行人“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似乎并不能完全说明新文学的全部意涵。他还以《山乡巨变》的研究为例比较了社会史视野与贺著采用的不同研究方法,认为两者都打开了政治,但是打开的面向和途径并不一样,而两种方法的对话空间很有意味,之间的张力蕴含了许多具有生产性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在发言中表示,贺著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政治建设中的政治主体性提供了一个论述角度。由于欧美学界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直接经验,对于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民族主义研究总体上很不够,而这本书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视角,探讨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其民族形式如何具体建构。这一研究不是在冷战的失败主义论调之下,而是努力把中国的经验提炼,进而普遍化。通过剖析民族形式,把开放的政治性认知与实践的转化方式揭示出来,这不仅仅是历史研究,而且具有当下的实践意义。另外,他还提出值得继续探讨的两个问题,即民族形式和科学的关系以及历史上民族形式视野与革命社会主义中国视野两种文明观的比较研究。

与会人员在静园二院合影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季剑青认为,此书显示了作者自觉的理论抱负,即以现代文学作为参照系重建当代文学史叙述甚至这个学科的内在原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原理性论述。在文学层面之外,作者更大的关怀是通过对这一时期当代民族形式建构的历史经验的反思和总结,呼应当下关于中国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自身主体性这一更大也更具开放性的问题。他追溯民族与民族形式在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流变,指出与苏联的非政治化甚至去政治化的民族形式不同,中国的民族形式包含强烈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普遍性的社会主义与独特的民族形式两者始终处于辩证的矛盾冲突和彼此塑造的过程之中;二,形式同样具有能动性,发挥了组织动员人民大众使其成为政治实践主体的作用;三,民族形式对活的传统的自觉吸纳,构建了极具包容性的融通古今、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认同形态。此外,他也提出疑问,如果我们回到当代中国文明论的叙述中去,是否可能找回原先内在于民族形式当中的批判性的人民政治视野?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静从新书的视野、思路和意义三个方面入手进行讨论。首先,她认为,贺桂梅以一种长时段全球性的文明论视野,回溯革命中国创制自身文化认同的起源时刻和发展历程,把当代文学的起点问题转化为一种原理性的探讨。其次,贺著将民族形式的创制理解为当代的起点,这一起源对于民族形式的自觉追求,决定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政治实践的具体展开方式,这一研究释放了起源考察的思想价值。最后,从作家的书写和文本形态出发,作者延展出了历史和理论的脉络,历史经验也由此转化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同时,李静也指出了书中的思考带来的挑战和困难,包括:面对内化到自身的西方理论和经验如何展开真正的对于西方的反思;如何更加历史化地辨析民族形式四个基本范畴各不相同的作用及其面对的问题;如何将少数民族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以及作家传播和接受状况纳入研究等等。

现场的热烈讨论
随后,研读会进入热烈而精彩的自由讨论阶段。与会学者就如何理解文学性、文学作为社会象征行为与社会实践行为的不同特质、能否在世界历史之外讨论中国经验、个人与国家建立关系的形式、当下文学经验的有效性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