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0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三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翻译中的‘他者’与成长中的‘自我’——贝尔曼《异域的考验》研读会”。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助理教授、《异域的考验》一书译者章文作引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段映虹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秦海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教授黄燎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孙凯,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副教授包慧怡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围绕安托瓦纳·贝尔曼的《异域的考验》展开讨论,讨论主题为“翻译中的他者与成长中的自我”。
引言环节
本次研读会围绕安托瓦纳·贝尔曼的《异域的考验》展开讨论,讨论主题为“翻译中的他者与成长中的自我”。活动伊始,章文老师简要介绍了此书的内容与旨趣。《异域的考验》带有强烈的为翻译(尤其是异化翻译)正名的动机。翻译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桥梁,在文化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贝尔曼所生活的时代中,翻译却始终低于原著,被视为次等的文本生成活动,处于被掩盖、被驱逐、被谴责甚至“女仆化”的境地。同时,翻译的窘境亦体现于译者所面临的双重背叛风险之中——一面被认为窃取了“他者”的作品,一面又可能造成对“自我”的文化品位或语言品味的冒犯。一般情况下,译者处于“自我”的文化语境中,不得不或多或少地改写原著,进而造成归化翻译长期占据主导的局面。出于对这一局面的不满,贝尔曼对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德国的翻译观进行了考古式梳理,以此揭示翻译在现代德意志语言文化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展现法国传统之外另一种更为尊重翻译的可能,并进而从史学、哲学和神学多个角度捍卫异化翻译的正当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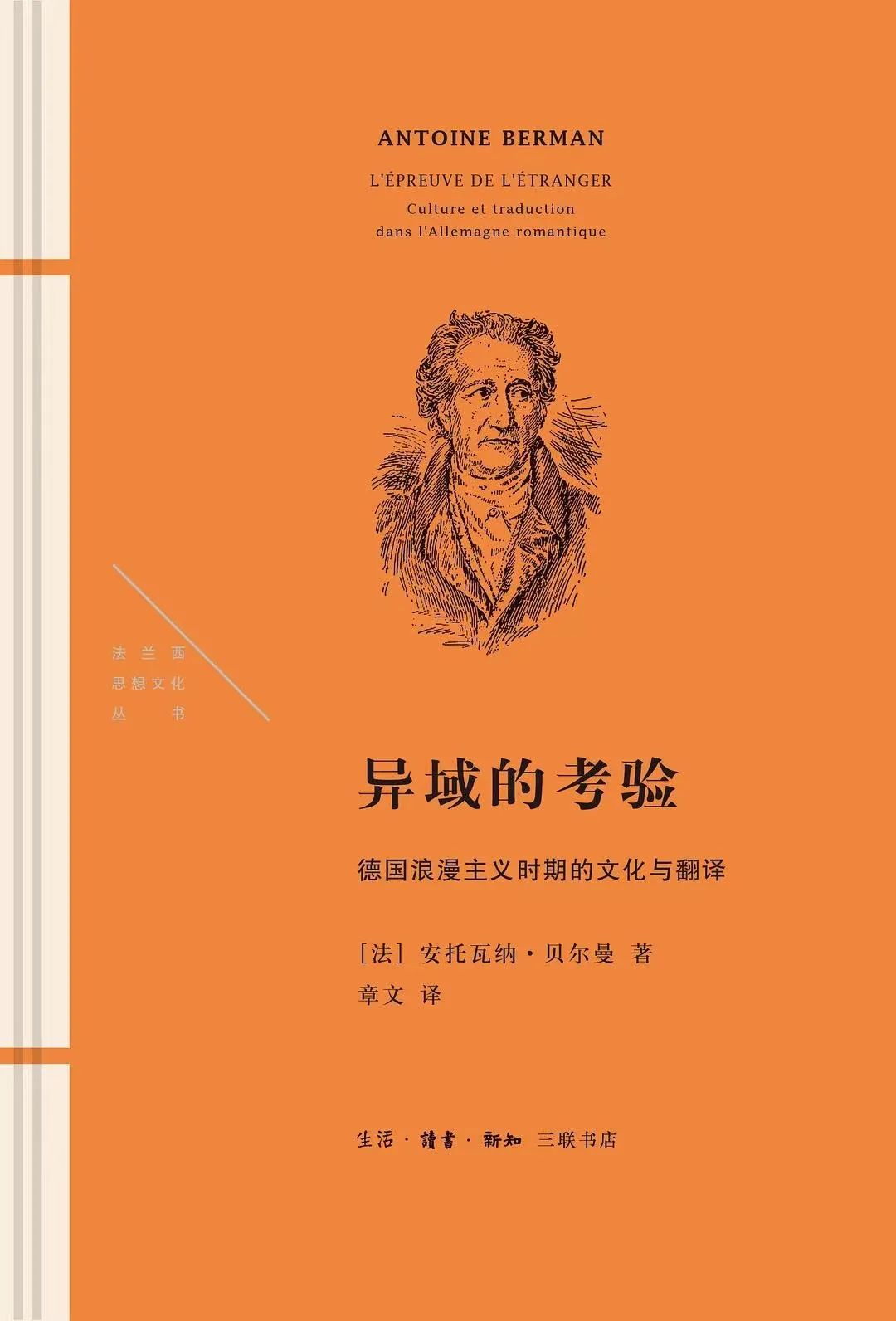
《异域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文化与翻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1月
具体而言,贝尔曼从以下三个层面为翻译与异化翻译正名:其一,“自我”呼唤翻译;其二,予以翻译其本所应得的地位,翻译不低于原著;其三,如果想要促进“自我”的成长,应当适度地摒弃归化翻译,采取更加尊重原文文字或原文形式的异化翻译。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德国经历了强烈的“翻译冲动”。这种“自我”对翻译的渴望,源于其时德国自身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不成熟,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较之于英、法的落后。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翻译,译介了古印度、古希腊、近代乃至同时代外国作家作品。古典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在翻译对德意志性奠基的关键作用、“他者”对“自我”成长的重要意义上达成了共识,文学作品中亦时时闪现着对“他者”或是远方的向往——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名为“他者”的人物一出场便代表着歌德本人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以及诺瓦利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中神秘的东方女郎祖莉玛所反映出的战争残酷性与他者诱惑力之间的矛盾,均为例证。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德国经历了强烈的“翻译冲动”。这种“自我”对翻译的渴望,源于其时德国自身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不成熟,尤其是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较之于英、法的落后。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们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翻译,译介了古印度、古希腊、近代乃至同时代外国作家作品。古典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在翻译对德意志性奠基的关键作用、“他者”对“自我”成长的重要意义上达成了共识,文学作品中亦时时闪现着对“他者”或是远方的向往——歌德《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名为“他者”的人物一出场便代表着歌德本人作品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以及诺瓦利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中神秘的东方女郎祖莉玛所反映出的战争残酷性与他者诱惑力之间的矛盾,均为例证。
既然“他者”对“自我”成长意义重大,翻译的重要性亦毋庸置疑。这一时代德国文坛群星闪耀,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派别——魏玛古典派与耶拿浪漫派——均赋予翻译以崇高地位。古典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歌德认为每一位译者都是民族的先知,而德语本身是一门世界语言,通过翻译,可以整合全世界各种文学宝藏,构建起真正的文学市场与普世的世界哲学。耶拿浪漫派的作品与文艺理论中展现着一种对永恒、终极、柏拉图式的理型(亦称“理念”)的追求,这样一种至高追求唯有通过文学作品的不及物性与直觉性方能实现,而这恰恰是翻译的特点。所谓不及物性,即艺术或文学脱离了触手可及的自然世界,不再是对自然世界的机械模仿,而是进入了一个至高精神层面,使其受众得以把握对世界刹那终极的感知;与原著相比,翻译显然更加“不及物”,因为它脱离了原文的语言现实,较原文相比有着更强的隐喻性。所谓直觉性,即对本质非分析性的直接捕捉,而翻译恰恰需要对原著特性进行直接体认,已经接近了浪漫派推崇的文学批评。

【奥】路德维希·多伊奇《检查》
东方题材绘画
1883 油画 40.3*27.3cm
在翻译地位已经如此之高、不亚于甚至超越原著的前提之下,魏玛古典派与耶拿浪漫派又基于对法国“不忠的美人”式翻译的共同反对,就“应当追求何种翻译”达成了共识。无论是古典派还是浪漫派,他们在施莱格尔给译者提出的两种翻译路径之间,都选择了异化翻译,即把读者带到作者的面前,而非让作者去迁就读者。这一路径选择背后蕴含着重建巴别塔、通向纯语言的期许,而译者无可企及的终点则是人类语言和文化的终极大同。在这一语境下,翻译超越了完全的经验论的层面,进入了形而上的空间。
评议环节

线下会议现场
随后,与会学者围绕本书及章文老师的引言展开热烈讨论。秦海鹰老师指出,本书总体将法国视为反例、将德国视为正例;但具体分析,贝尔曼对德国的魏玛古典派与耶拿浪漫派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且两种流派的翻译观在客观上也存在区别。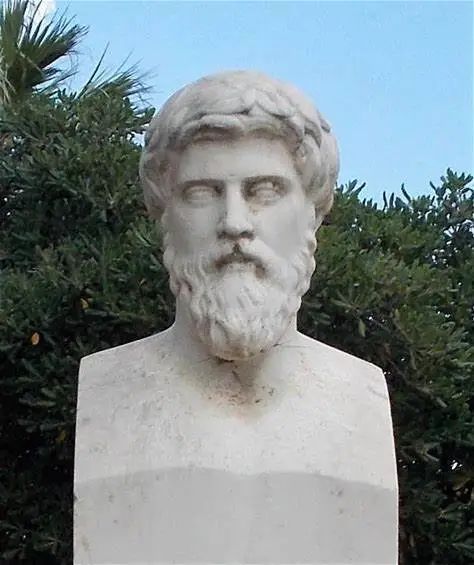 耶拿浪漫派秉持广义的翻译理论,将诗歌、翻译、阐释、哲学纯思辨视为同义词,贝尔曼形容其为“思辨的”、“诗歌的”、“不及物的”、“独白的”;魏玛古典派则秉持狭义的翻译理论,贝尔曼称之为“反思的”,而非“思辨的”、“对话的”、“独白的”。关于贝尔曼对翻译思想的独特贡献,秦老师指出,虽然在贝尔曼之前,许多译者已然关注到归化(更靠近母语)与异化(更靠近外语)作为翻译的两极所呈现的张力,但贝尔曼率先指出这两种基本方法的选择反映了译者的伦理态度,即译者是否在语言层面上尊重他者,是否忠实于原作的差异性。此外,虽然贝尔曼将法国的翻译传统视为反例,但法国的翻译传统同样对法国民族语言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举例而言,生活于16世纪的雅克·阿米欧翻译的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极大地丰富了法语的表现力,促成了“法语大散文的诞生”,塑造了蒙田的散文风格,也奠定了法语写作的“长句子”传统,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普鲁斯特、格拉克等20世纪作家。贝尔曼本人深受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思想影响,《异域的考验》这本书或许可以看作是法国的解构思想与德国古典浪漫主义时期翻译思想的隐形对话。
耶拿浪漫派秉持广义的翻译理论,将诗歌、翻译、阐释、哲学纯思辨视为同义词,贝尔曼形容其为“思辨的”、“诗歌的”、“不及物的”、“独白的”;魏玛古典派则秉持狭义的翻译理论,贝尔曼称之为“反思的”,而非“思辨的”、“对话的”、“独白的”。关于贝尔曼对翻译思想的独特贡献,秦老师指出,虽然在贝尔曼之前,许多译者已然关注到归化(更靠近母语)与异化(更靠近外语)作为翻译的两极所呈现的张力,但贝尔曼率先指出这两种基本方法的选择反映了译者的伦理态度,即译者是否在语言层面上尊重他者,是否忠实于原作的差异性。此外,虽然贝尔曼将法国的翻译传统视为反例,但法国的翻译传统同样对法国民族语言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举例而言,生活于16世纪的雅克·阿米欧翻译的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极大地丰富了法语的表现力,促成了“法语大散文的诞生”,塑造了蒙田的散文风格,也奠定了法语写作的“长句子”传统,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普鲁斯特、格拉克等20世纪作家。贝尔曼本人深受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思想影响,《异域的考验》这本书或许可以看作是法国的解构思想与德国古典浪漫主义时期翻译思想的隐形对话。
黄燎宇老师主要分享自己在文化史层面受到的启发。他很高兴通过阅读《异域的考验》找到两个很有用的“文化标签”。第一个是民族标签,即德国是一个翻译大国。本书关注的时段是德国的“翻译热”时期,其翻译热情之高涨,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表现为文坛主力均从事翻译工作——无论是古典派的歌德、席勒、赫尔德、维兰德,还是浪漫派的蒂克和施莱格尔兄弟,都留下了重要译作。倘若追溯德国作为翻译大国的缘起,路德是不能忽视的关键角色,他是德意志民族身份的生成器,将德国带上了语言成长的特殊道路,赫尔德、海涅、恩格斯、尼采对路德均有很高的评价。第二个标签是时代标签。从法国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至歌德去世的1832年之间,德国在文化领域上取得了诸多辉煌成就。借用霍布斯鲍姆的概念,德国文化革命,或可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合称为“三元革命”。这一时期,德国文坛上魏玛古典派与德国浪漫派“双峰并峙”——两派均给德国的历史与文化打下深刻烙印,歌德与魏玛甚至成为陷入四面楚歌的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救生圈”。有人把这一时期称为“歌德时代”;有人则认为古典派与浪漫派并非截然对立,而是有许多相似的观念与共同的秩序追求,彼此有密切关联,所以把歌德也纳入“浪漫主义时期”;有人认为这一时期古典派和浪漫派平分秋色,所以称其为“古典-浪漫时代”;还有人考虑到这一时期的德国人尤为热衷于文化修养,所以称之为“文化热时期”。黄老师认为,读了《异域的考验》,我们有理由把这一时期命名为“翻译热时期”。文化史之外,黄老师也分享了针对德国浪漫派的翻译观的体会。在德国浪漫派看来,一切从自然语言到艺术语言的转换都是翻译。这是一种罕见的大翻译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一切文学创作都是翻译,一切文学阅读都是翻译,一切文学批评都是翻译。因此,文学翻译就成为对翻译的翻译,译本比原作更远离自然语言,所以高于原作。这是德国人说奥古斯特·施莱格尔的莎士比亚译本超越了莎士比亚原作的理论基础。黄老师进一步指出,归化与异化的译法选择反映了译者的文化心态。18世纪末,德国人翻译外文著作多用异化的译法,反映其谦虚、开放的文化心态;而当代德国人翻译中国当代文学则多用归化的译法,这反映其强势文化的自我定位。

【德】卡斯帕·弗里德里希《海边的修道士》
1810年 油画 110 x 171.5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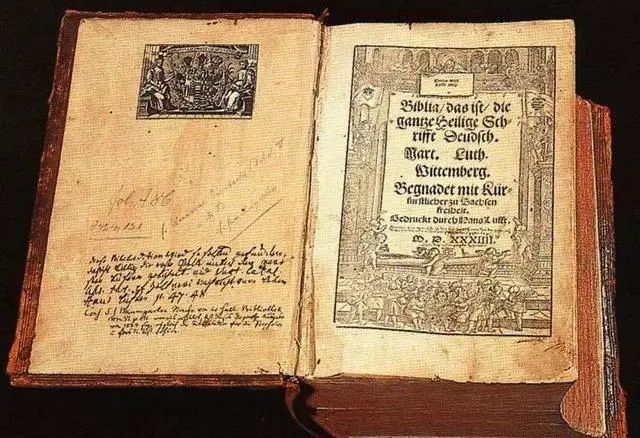
路德故居展出的路德翻译版圣经
孙凯老师从四个角度解读本书。第一,巴别塔神话。按照《圣经》的叙事,人类建造巴别塔,神变乱了语言,离间了人类。贝尔曼将这一宗教叙事视为历史事实,并承袭本雅明《译者的任务》的观点,认为需要通过直译的方式重建前巴别塔时代的纯语言。贝尔曼的老师梅肖尼克与贝尔曼本人都受到了本雅明思想的滋养,而梅肖尼克“得其声”,强调翻译要忠实于节奏;贝尔曼“得其形”,强调翻译要忠实于文字。第二,德国浪漫派。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浪漫主义的定义、外延与内涵均有所差异。贝尔曼虽为法国人,他的浪漫主义却源自德国传统。德国浪漫主义认为历史是一个从单一到不和谐再到和谐的过程,即先由一分为多、又从多重新归一。这一逻辑在《圣经》的宗教故事、语言的发展、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等层面均有生动的体现;贝尔曼对于纯语言的追求,亦出于此。其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贝尔曼将翻译的现代性思考分成三个维度:翻译的历史、翻译的伦理、翻译的精神分析。精神分析包含三个层次。第一,任何人心中均有用外语破坏、改造母语的冲动。第二,不要过分相信译者在序言、跋语中的自我表达,而要回到译文,由其翻译实践体会其翻译思想。第三,贝尔曼本人便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对象。事实上,贝尔曼只不过是贝尔曼的“自我”,本雅明才是贝尔曼的“本我”;若放置于西方哲学认知论的两条线索上进行观察,亚里士多德是贝尔曼的“自我”,柏拉图是贝尔曼的“本我”。第四,翻译阐释学。如果说精神分析研究的是谎言,那么阐释学研究的就是误会。翻译阐释学,则是研究一个译本在一个国家或地区造成的误会。人类的历史并非由真相造就,而是由对真相的阐释造就。贝尔曼所写的德国人,是其看到、理解的德国人,不等于德国人的本来面目。因此,推进贝尔曼研究,需要法语系学者与德语系学者的通力合作。

《圣经》记述的巴别塔神话
包慧怡老师随后发言。她首先介绍了中世纪作者观。中世纪有不少阐释“何为作者”的理论,却很少讨论“何为自我”、“何为他者”。在中世纪写作者看来,“自我”与“他者”并不泾渭分明,而是互相生成的关系;作者就是“做书的人”。 全民接受基督教带来了书写文化的改变。在全民接受基督教后的1至2世纪后,即公元7世纪左右,不列颠岛上开始出现书面而非口述形式的古英语文本。至13世纪,波纳文图拉将“做书的人”分为四类:写别人的字、一个字也不改的是缮写士;写别人的字、把别人的片段汇在一起的是汇编者;同时写自己的字与别人的字、以后者为主的是评论家;写自己的字和别人的字、但用别人的字解释自我的人才被称为作者。翻译者的工作是用自己的字表达别人的字,自然归于作者一类。为更好地阐释中世纪作者观,包老师进一步介绍了乔叟这一英国14世纪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乔叟的翻译工作为其文学创作打下了重要基础。在翻译过程中,乔叟亦对中古英语进行了重要的改造。中古英语的前身古英语风格阳刚、铿锵,而乔叟则从古法语中引入了大量精巧的修辞与典雅的爱情词汇。乔叟并不将这种引入视为法语对英语的入侵,而是将英语视为仍需进一步扩容的空间。对于中世纪作家而言,翻译乃“渡津”,译作往往是通向创作的起点——渡津是为了汇入乃至开拓更广阔的河川。庞德从翻译中国古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创设意象派诗与“三位一体”译诗论,也是一个重要例证。
全民接受基督教带来了书写文化的改变。在全民接受基督教后的1至2世纪后,即公元7世纪左右,不列颠岛上开始出现书面而非口述形式的古英语文本。至13世纪,波纳文图拉将“做书的人”分为四类:写别人的字、一个字也不改的是缮写士;写别人的字、把别人的片段汇在一起的是汇编者;同时写自己的字与别人的字、以后者为主的是评论家;写自己的字和别人的字、但用别人的字解释自我的人才被称为作者。翻译者的工作是用自己的字表达别人的字,自然归于作者一类。为更好地阐释中世纪作者观,包老师进一步介绍了乔叟这一英国14世纪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乔叟的翻译工作为其文学创作打下了重要基础。在翻译过程中,乔叟亦对中古英语进行了重要的改造。中古英语的前身古英语风格阳刚、铿锵,而乔叟则从古法语中引入了大量精巧的修辞与典雅的爱情词汇。乔叟并不将这种引入视为法语对英语的入侵,而是将英语视为仍需进一步扩容的空间。对于中世纪作家而言,翻译乃“渡津”,译作往往是通向创作的起点——渡津是为了汇入乃至开拓更广阔的河川。庞德从翻译中国古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创设意象派诗与“三位一体”译诗论,也是一个重要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