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杨庆堃专题”推送的是他为韦伯的著作《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的英译本所写的一篇“导论”(节选)。就像他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杨庆堃对于宗教的研究关心的问题是:在中国社会的生活和组织中,宗教承担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与组织发展的基础,而这些功能是以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这篇导论是理解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重要参考。他认为韦伯的这本著作所关心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领域,它是以中国社会的“物质”结构为基础,进而讨论儒教和道教的“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杨庆堃肯定了韦伯提出的问题,即“士的地位与性格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之间,有何种关联?”虽然他认为这个问题还没有被很好地解答,但不管是对于士绅的研究,还是对于地方政府的研究,都是燕京学派的同仁们热切关注的主题,而对于这些主题的思考都可以从韦伯的这本著作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这篇导论的意义就在于杨庆堃对这些研究主题的重要性有着极为明确的认识。
本篇“导论”中文版见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附录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因原文较长,分上、下两篇推送,以飨读者。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导论(节选·上)
文 | 杨庆堃
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
在这本《儒教与道教》里——葛斯将之改名为《中国的宗教》为的是避免落入意识形态的窼臼里(the isms)——韦伯继续他在《新教伦理》中的主题,试图就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及儒教与道教的特殊面貌,来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相对照。阅读此书时,如果读者太将注意力钉牢在此一经过翻译的书名——《中国的宗教》——上的话,那么他必定会感到相当的困惑,因为书本所处理的范围要远超出宗教的领域。其实,在英译本的249页里,有141页,或者说有一半以上的篇幅,主要是在描述中国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特性,并将之比对于西方及其他社会的相类层面,而仅在某些段落中偶一提及宗教。只有在本书的后半段里,宗教的理念与价值才是被集中讨论的主题。况且,韦伯并不将儒教视为一个奉神的宗教(theistic religion),而仅是某种伦理学说,因为它虽然容忍巫术的施行,然而却缺乏形上的基础。若视本书为一种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伦理价值及宗教的研究,并注意这些方面特别有关于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发展的特性,将更有助于读者去掌握韦伯的主题。
关于中国社会结构之特性,之所以要花那么大的篇幅(第一章到第四章)来加以描述,显然是因为韦伯想要在仔细地检视过“物质的”因素之后,再将重点摆在致使理性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萌生的“精神的”因素上。下面几页里,我并不试图为本书做适切的摘要;而是想就我所了解的范围,将韦伯在主题上的论证作一番疏理澄清,并将其中的某些论题,就现今中国的社会研究上所得的成果加以讨论。
本书共分为三部分,这明白显示出韦伯在论证上的逻辑统一性。首先,韦伯检验了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及社会等各层面,描绘出各层面相互交融影响后的结构或“物质的”特性,其中各点或有利于或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换言之,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之特性来说,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在“物质的”条件上并无重大的差别。其次,韦伯将儒家的价值体系与基督新教的伦理作一明显的对比,认为前者缺乏后者所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力动因(dynamic motivation)。在第三部分,韦伯指出道家负面的、保守的价值系统,无法发展出一强而有力的社会取向之态度,以走向资本主义之路。以此,韦伯将决定性的差别因素归之于儒教与道教在价值上的消极与传统特性,并用以解释何以资本主义发展于西方而不展现于中国。
然而,每一部分及每一章里的数据处理,在逻辑上都同样的不够清晰。韦伯的兴趣并不在于有系统地呈现出中国社会结构及其价值体系;相反,他的主要目的是在将这些层面与西方社会的类似成分做一对比。问题就在于:他并没有明白交代,他用来选择与安排各比较项目的理论根据是什么?他的主要论点因此经常变得模糊不清,尤其在第一部分里更是如此:他处理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性,却冠之以“社会学的基础”的名目。
按照他自己在第一部分里所安排的顺序,韦伯在中国的社会体系里选择了五个与近代资本主义要件有关的主要具体项目:货币制度、城市与行会、家产制国家与血缘组织以及法律,来加以讨论。如果我们将结构因素当作是一个范畴的话,我们可能还应该再加上,韦伯在第二部分第一章里所论及的,作为一个身份团体的知识分子。
韦伯以货币制度与城市作为讨论的起点,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因素与西方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之蕴生特别有关系。其次,他转而讨论中国社会的两个特出层面:家产制国家与血缘组织——以大小来说,是为组织结构上的两级。紧接着的主题是法律,也许是因为其特性受到国家与血缘两大系统之本质所影响。其他的许多主题,尤其是制度在历史上的发展,皆散置于以上几个主要的项目里被论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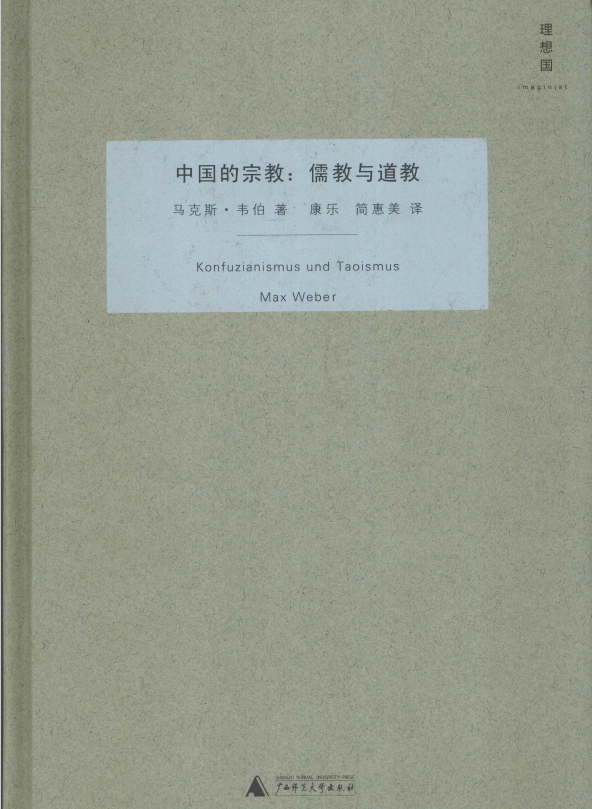
马克斯·韦伯著《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韦伯以货币为主题来开始他的研究,正因为他充分了解到货币在他的经济社会学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货币能扩展经济交换的领域,有助于财富的追求与累积,并可作为经济价值的衡量标准,以评量不同性质的物质与劳务的相关经济意义,因此,在订定预算时便能计算出利得或损失。由于货币有以上这些重要的功能,因此,中国在历史上无法建立起一套有效率的货币制度便是缺乏资本发展的征兆,并且也阻碍了任何有意义且大规模的理性资本主义之发展。然而韦伯并未指出,十八世纪以来,银的供应量即不断地增加,这便可能激发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实际上并未发生)。
城市蕴生了西方的资本主义,但在中国却不具相同的功能,其原因是中国的城市缺乏政治上及军事上的自主性(autonomy),而且也缺乏作为共同体(corporate body)组织上的统一性(organizational unity),而西方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经营之理性发展所依恃的财政与法律背景,即是靠着此种自主性与统一性才得以坚实稳固的。韦伯认识到行会在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里有其中心地位的重要性,并且他认为行会在组织上的自主性是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由于行会的特殊权益未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因此不得不发展成具有极端自足性功能的形态,而无法像西方那样,发展出一套正式的法律,以作为“一既自由且能共同规范的共商组织”之形成基础。
强调货币与城市乃是影响一个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战略性因素,韦伯自然有其充分的合理说法——不论是在理论上,或者征诸于历史。虽然最近有资料显示,某些政府保障行会的垄断与特权的现象确曾出现,这与韦伯的论断相违,然而还是有些做中国都市社区研究的学者支持韦伯的说法,认为中国的都市社区并不具有一个共同体的功能。自韦伯时代以来,传统中国的都市社区研究实在乏善可陈,因此还未能有既充分又可靠的资料可对韦伯的观察所得——以极不充分的资料而得出惊人的敏锐判断——加以系统性的评论。一直到50年代的中期,我们才看到有某些中国内地的学者开始对中国的都市经济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有系统的研究。一些关于传统商人阶级和工商行号、工匠技艺之特质——一些韦伯所没有机会加以检验的重要层面——等极具意义的资料也已经出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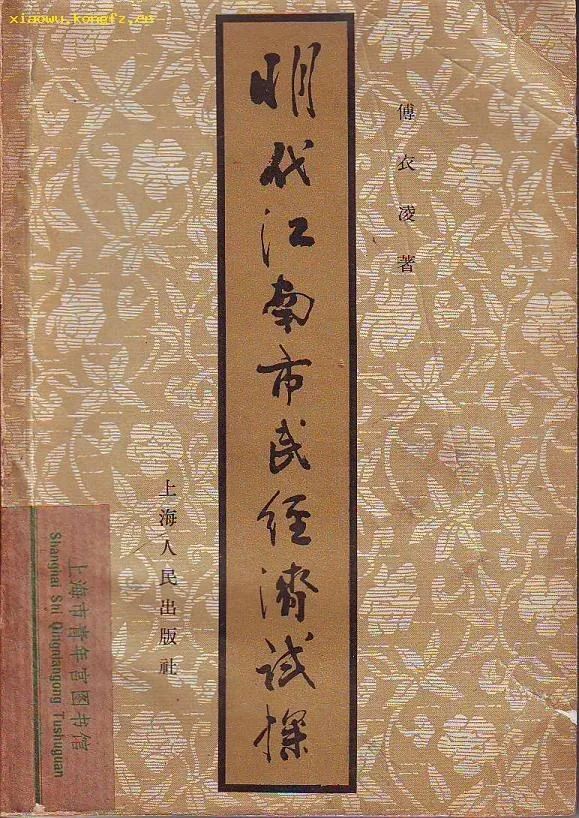
50年代的中期以来内地学者对中国都市经济及“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的代表著作: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新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韦伯将中国城市之缺乏军政自主性(politicomilitary autonomy)归因于帝国统一的过早形成——所有的民政、军事皆置诸国家官僚体系的集中掌握之下。封建制度瓦解之后,此一大一统的帝国所具的军政力量是如此的完整无缺,以至于个别城市所能自其中获取资源以资自主的机会,实在非常有限。就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机缘来说,这个中央集权的帝国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意义便成为值得研究的问题。韦伯是从以下这些有利的检查点来检验此一帝制国家并对其所蕴含意义加以分析:一般的特性、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中央—地方关系与家产制官僚体系,农业政策与乡村管理。
帝国的统一与和平有其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特性,亦有其不利的一面。人口与物资能够在像欧洲一般辽阔的领土上自由地迁徙、流通,而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阻碍,这显然即是其所蕴含的有利条件。就其不利的一面来说,包括:城市缺乏其政治的自主性——一种能为资本主义企业提供既适切且富刺激性的环境之自主性。以统一与和平来取代封建国家间的敌对与争斗,也意味着不再有竞争的压力,迫使各国相竞以理性化的手段来改进国家利益与生存所必须的官僚与经济组织。此外,由于国内的和平,使得促成西方政治资本主义发展的战债与作战佣金也就无由产生了。
帝国之统一与和平的建立与维持有许多影响力,这些也都关系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一是在中国的封建诸国间很早就发展出统一的文化。而更重要的是皇帝与他的官员执掌了宗教的功能。这就削弱了足以与俗世政权相抗衡的教士阶段的有利地位,使其无法威胁到帝国内部的统一。正是这种对和平、秩序与宁静的强调,使得狂喜与悲怨等感情上的过激都可不断地通过官方的仪礼而剔除净尽。不具任何官方地位的民间宗教则总是趋向多神的信仰,这是使得民间宗教无力向国家统一力量挑战的关键因素和不利影响。以上种种缘由造成了一种情形:既没有一个教土阶层,也没有一支独立的宗教力量,能够为社会经济秩序带来激烈的变革,而促成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帝国的统一与和平并不意味着高度中央化的行政体系能够通贯于整个帝国。一部中国史里多的是中央政权与地方利益不断争斗的记录。中华帝国最具特色的家产制官僚体系与源远流长的组织无法完全解决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冲突,也无法有效地理性化二者的行政体系。
官僚人员的递补是由士人经过考试而来的,因此,官僚地位的形成,既不基于出身,也不基于超自然的考虑或神灵的恩典。这种普遍无私的现象有助于官僚体系的理性化。其他的层面还包括:三年一换的公职任期制,不得任官于乡里的限制,中央可任意召遣官员的充分主动性——以防制官员在地方上发展其久远的利益而对中央政权有所损害。
但是此种中央化的措施却有其反效果:它会削弱正式的官僚统治与民间生活之间的关系。而且由于中央权威的膨胀,致使地方行政体系无法理性化。配额的税收制度使得官员不但可以应付行政的花费,而且只要交出分配的税额,他就可以从官方的税收以及非官方的收费和“赠礼”中谋利。公家与私人的财产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分。结果使得“整个帝国就好像一个由大祭司带领着许多地方老大所组成的联邦体”,中央企图统一与合理化地方的行政单位的努力自然要受到挫折。再则,儒家君子不器的观念使职业的分工难以形成而减低了官僚体系的合理效率。据韦伯看来,官僚分子都是些不器的君子,那些专门的工作便都委之于吏役与幕府去做。这些官僚体制上的特质,再加上缺乏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下的广袤领土,在在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正式行政管制力量降到最低点,而且通常几乎等于没有。此种情形所蕴涵的经济意义即是:地方上在形式的社会政治秩序方面的薄弱,不足以构成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法制基础。
在本书的许多部分及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韦伯对中国的官僚体制与士人都做了相当精彩的描述。此后,将官僚体制与士人认定为影响中国社会本质的两大要因,并以之为研究主题的学风大盛,而这些晚近的研究也大多赞同韦伯的观点与论断。韦伯对于中央官僚系统设法防制官员与地方利益勾结相连的分析是尤其深刻而精确的。这些防制的措施使得当政的官员无法直接有效地掌理地方的事务,并因此而增加了介乎官员与民众之间的非公职的幕僚、佐员与吏役等角色的重要性。
这种中央正式行政权无法直接达于地方百姓的情形,最近已大致为对中国地方政府甚有研究的瞿同祖加以证实。瞿氏所证之史实明白指出,府县级的传统中国地方政府是由少数中央任命的官员主持的正式官僚组织,以及主要由知县私人幕友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共同治理,而由后者直接处理地方问题,然而其方式通常却逾越官僚组织之正式法规。由中央任命的官员发现想要穿透地方势力的紧密控制,或是以正式法规来取代他们的治事方式,是非常困难的,甚而简直是不可能的。这基本上与韦伯所分析的情形不谋而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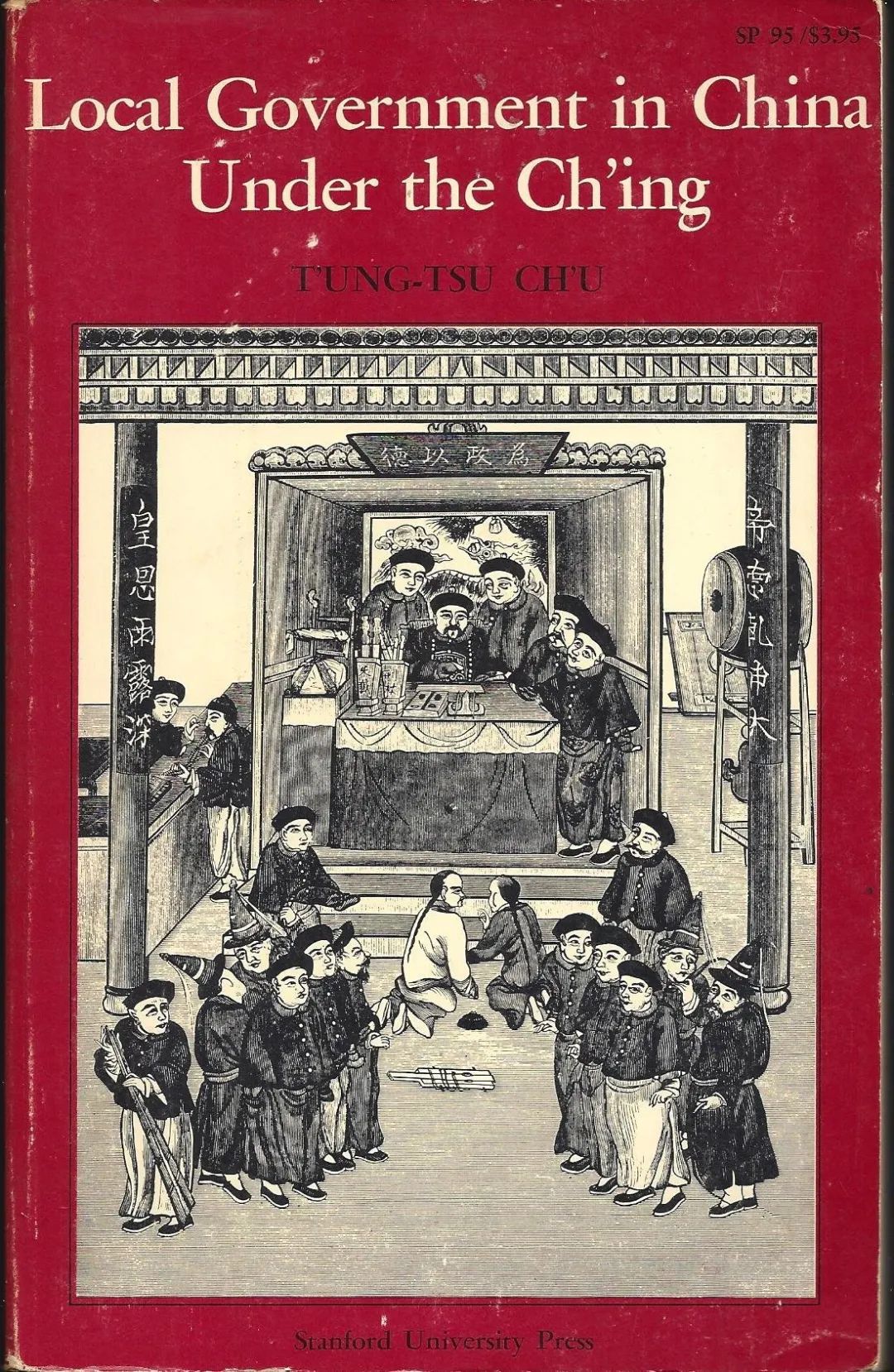
瞿同祖所著《清代地方政府》
韦伯分析中国史上的农业政策与乡村管理所采用的资料似乎甚为不妥,而且在事件的逻辑关系与时间先后顺序上,他的数据处理方式也相当令人困惑。关于王安石于十一世纪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改革,韦伯的主要资料来源显然只限于俄人伊凡诺夫(A.J.Iwanoff)早期在这方面的研究。许多新近的研究已使得乡村社区的政治秩序、或王安石的变法呈现了更清楚的面貌,而不只是像韦伯所提出的简单景象:以常平仓或集体责任体系(保甲,或如韦伯的用语:连带责任社团)来勾勒出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秩序的特色。不过,在历史上的土地改革,及其影响所及的农业生产方式方面,韦伯虽然受到材料不足的限制,但是其研究成果却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
韦伯指出中国农业史上的一项根本事实:历史上曾不断发生农业危机,而且经常由土地的重新分配、限田和自由垦荒(可与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政策作比较)等措施来加以补救。
历史上的土地改革现象虽然在西方未获重视,但最近几十年来却广泛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然而无论是中国或是西方,凡是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学者,无不以人道主义、平等主义,以及农村经济政治秩序之稳定等观点来解释历史上的改革办法。惟独韦伯提出这样一个不同的看法:过去两千年来许多土地改革的成功,致使农地被分割为无数的小型耕地,构成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面貌。对韦伯来说,这正可解释资本主义在中国无可发展的原因:“由国家所推动的各种土地改革措施导致……中国无法产生合理而大型的农业经营……土地的不断分割阻碍了技术的进步;即使货币经济已有所发展,然而传统仍占上风。”
中国的血缘体系正如帝制国家一般,在许多方面阻碍着合理经营的发展。追求财富的一个重要的模式即是:通过家族的资助,培植家中的一员接受教育、中试为官,以行其内部的“掠夺式资本主义”(booty capitalism)。此种家庭投资的方式不会发展成为“合于经济理性的合作企业”。庞大的血缘组织具有许多因应个人社会与经济需求的功能,因而阻碍了个人的独立性与个体性。家庭副业(如纺织)的普及也阻碍了独立工业生产方式的发展。血缘组织强固的凝聚性、族中长老极具效力的威权,以及乡村的自治阶层等,在在将有效率的正式行政当局限制在城市的范围内,行商于广大领土上便得不到法律与秩序的保障,而此种保障正是发展资本主义所必具的条件。血缘关系也保护个人不受外界的歧视与屈辱,这也有碍于现代大型企业所要求的工作纪律与开放市场上的劳工选择。准此,“大型的私人资本主义工厂便无从于历史中觅其根源。”
中国社会里的家族特色,自韦伯的研究之后,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学术注目与继起研究。一般说来,近人的研究成果大体与韦伯的解释并无抵触之处:中国的血缘体系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利的影响。不过,韦伯所运用的资料存在着地区错置的问题。他所论及的血缘关系现象大多发生在乡村地区,然而,城市才是资本主义所应发展的地区;在城市里,血缘组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城市体系里,我们不知道血缘组织是否也会像韦伯所断定的那样有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恰当的资料能够显示中国的家族在都市中心所具有的功能与特色,所以这个问题自然也就得不到解答。至于中国史上是否有过大型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根据晚近的研究显示,至少在许多传统工业方面,例如丝织业与陶瓷业,其企业的规模与组织的复杂性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不过,至今在这问题上所能应用的资料仍然非常有限,是故亦不能对韦伯的解释有一可靠的评估。
在中国社会结构的众因素里,支配着传统中国的实质伦理法律,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很明显地具有负面的影响。现代的资本投资需要有理性的,以及可估量的法律与司法程序来运作。但是富有理性及可估量性的形式法律在中国这个家产制国家并不发达,因为任何形式的律则与固定的程序都将限制了世袭的权力与特权。中国的律令“毋宁是编纂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约”。韦伯的这一项观察,已全然为瞿同祖所证实,瞿氏指出伦理的以及礼仪上的规范,在中国法律的建构上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实质伦理法律相当有利于世袭君主在政治上的权宜与伦理上的要求。但是实质伦理法律无法发展出明确的形式与程序。形式法之所以无法在传统中国获得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有部分是因为血缘组织具有特别高度的影响优势,以及缺乏一个对法律的订定特别感兴趣的策略性团体,亦即职业的法律专家。因为行政与司法都已被吸收到公务系统的职权里。
韦伯虽然看到中国有许多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但他也提出了许多有利的因素:例如没有以出生为准的身份限制、自由迁徙和在自己的家乡之外定居、职业自由、没有义务教育与义务兵役,以及没有借贷与贸易上的法律限制。“就一个纯粹的经济观点而言,真正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已有可能发展……”资本主义之所以无法在中国出现,基本上还是由于缺乏一种像禁欲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特殊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