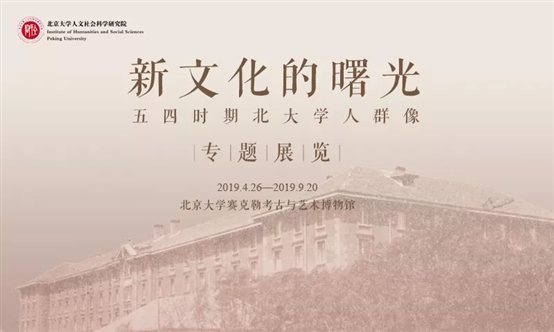
北大学人:新文化运动的光荣和骄傲
“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开展致辞

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致辞
很高兴也很荣幸来到北京大学的新校区,参加“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时期北大学人群像”展开幕式。我来自北大老校区,就是沙滩五四大街的北大红楼,现在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北大举办这个展览,主题鲜明,寓意深刻。我馆给予协助,提供了一些展品,很应该。我的同事和朋友中有不少北大校友,我曾对他们说,红楼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从京师大学堂创立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了,北京大学以卓越的成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建立了巍峨的丰碑,在国民中也有极好的口碑。在我们馆的纪念品部,我常看见家长给孩子购买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复制件,鼓励他们报考北京大学。
我谨代表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对北大成功举办“五四时期学人群像展”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把北大新老校区紧密联系起来了。我们都在为此辛勤工作。

本月中旬,我馆举办了“在文学和历史之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从政治、思想、文学等领域跨学科、多角度探讨这场运动的历史意义和巨大影响,大会特意安排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者第一个发言。本月23号,我们在红楼内举办了《五四现场》展览,用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的文物、图片、媒体报道等,反映运动的过程,引导观众回到历史现场。当然,观众回到的最有意义的现场就是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源地。这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现在得到妥善的保护,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成立以来,致力于搜集和整理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文物资料,并把研究成果展示给观众。五四运动,起因复杂,过程激烈,影响深远。对此,我们坚持大历史观,不偏狭,不武断,不歪曲,不遮掩,以诚实求真的态度研究历史,以温情和善意对待先贤。在《五四现场》展览后,我们还要推出《国民:1919》展览,挑选近百件文物,全景扫描和重点聚焦相结合,表现五四运动发生那一年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状态。此外,我们还有新文化运动的专题展览《新时代的先声》正在全国多个省市巡展。
北京大学在赛克勒考古和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新文化的曙光》,与我馆的展览《新时代的先声》,可谓异曲同工,用两种物质形态表现了那个时代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声,一个是光,一个是呐喊震醒噩梦,一个是灵光开启智慧。我们一个发声,一个发光,配合得默契。

以北京大学为重镇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北大学人一面引进国外先进思想,提倡民主,崇尚科学;一面继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尊崇经典,疏通源流。出现了一批思接古今、学兼中西、旧学深邃、新知深沉的大师,推进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五四运动前后,人们在称呼北大时,直接称之为“大学”,可见北大是大学中的大学,是中国现代高等学校的楷模。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都与北大密切相关,是北大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明证。
鲁迅1917年为北大设计的校徽,图案简约而不简单。他把篆体北大两字画成三个人,上二下一,一大两小。我揣摩,他不一定是要表现大学师生比例应该一比二,也不仅仅是演绎先哲的教导“三人行必有我师”。底部那个“大”字——我们可以称之为“大人”——从形体上看,却是一副很吃力的样子,腿都弯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负担很重——肩膀上坐着两个人。我觉得,鲁迅把师生之间的关系画得清明透彻,形象生动。老师——也就是今天这个展览题目中所说的“学人”——是学校的主体,是根本,是基础,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托起下一代,劳心竭力培育青年才俊。鲁迅把老师们画得这么辛苦,老师们会不会埋怨他呢?不会,鲁迅是在向老师们致敬!北大把这个校徽图案用了一百多年,可见老师和同学们是认可的。鲁迅在《我观北大》中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一百多年来,北大正像鲁迅期望的那样,代代传承,为国家培养无数优秀人才。
我们要珍视学人,展览的主题让人心动。在今年的一系列纪念活动中,我馆还有一个虽然简单但具有象征意义的活动,就是选择新文化运动八位先驱的生平事迹、著作手稿和书法墨迹,制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文化八大家”展览。这八位名家是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他们在一个时期,一个城市,一个学校会合齐聚,造就新文化的灿烂星空。他们与“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唐宋古文运动的大师们一样,把中华文化引向一条自主自信、健康向上的道路。新文化八大家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又都曾留学海外,他们是中国文化转型的见证者、中外文化交流的亲历者和文化创新的实践者。五四和新文化的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比中国历史上其他的文学运动更开放、更包容,更恢弘、更壮阔、更集中、更有力。我在展览的前言中特别写了一句:新文化八大家多为北京大学教职员和《新青年》杂志同仁,这是北京大学的骄傲和光荣。没有学人,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影响如此巨大和深远的五四运动,就没有百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北京大学学人群体中大师辈出,八家之外还有很多,今天的展览表现得很全面也很系统,莘莘学子一定能从中得到教益,汲取力量。这昭示我们,学人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珍宝。社会的进步,教育是根本,学术是重心。学术是社会发展高度的标尺。
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开辟未来。我们研究百年历史,有时可以用发展的脉络和现实的经验来印证。例如,我在做“国民:1919”展览时发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勤工俭学热潮中派出大批学员到法国,60年后,这些学员中的一位领导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把中国引向好的、向上的路途。历史事件之间有因果联系,有前后照应,我们面对一百年前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常常小心谨慎,不敢轻易下判断,生怕唐突先贤,厚诬古人。我们可以从自身经验设身处地想象和揣摩他们的心思。例如,我们经历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全民动员“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壮阔场景,就可推断出四十年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得力于国民的求知热情和知识的丰富积累。以此类推,现代中国的巨大变革,百年来学人群体功不可没。
我在博物馆工作,我认为办好博物馆、纪念馆,必须注重学术,所以经常讲“学术立馆”的理念。我刚才走进校园,突然想,大学现在的办学理念是什么呢?是“学术立校”吗?又觉得这样说等于什么也没说。研究学术是大学的天职,这里的一草一木,无非学术。北大的先辈百年前就提出要建立“学术社会”,的确是真知灼见。社会上每个行业都需要学术支撑。借此机会,我请求展览的主办方之一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多派优秀毕业生到博物馆、纪念馆工作,在“学术立馆”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今天上午我在红楼,看到熙熙攘攘的参观人群,大多是高校学生,青春洋溢,生机活泼。其中想必有北大的学生。我这里要发出一个邀请:欢迎北大的老师和同学们常回红楼老校区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