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之一,北京大学一百年来思想文化的创造、学术传统的更新,都与五四有着各种各样的承续关系;而五四运动也深远地塑造着北大师生的精神气质与思想传统,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和科学文化最为敏锐和坚韧的探索者、开拓者。回望五四,对五四的再评估与再诠释,意义非凡。有鉴于此,文研院于2019年3月30日举办“五四与现代中国”学术论坛,邀请海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相聚北大讨论交流。
本文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讲座教授王德威在论坛上的主旨演讲,并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5期”百年五四”纪念特刊,内容以正刊为准。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鲁迅、韩松与未完的文学革命
——“悬想”与“神思”

王德威教授
五四运动以1917年胡适、陈独秀等所号召的“文学革命”为肇始点。由文学所承载的批判性及创造力,成为启动、支撑革命想像和实践最重要的资源。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曾有名言:革命的意义无它,即在于引发人同此心,共创新猷的感染力(pathos of novelty)。这一革命性的感染力见诸于五四,就是文学。这里所谓“文学”,不再仅限于学院规划的纸上文章,或文学史所罗列的大师经典,而是一种应答并改变世界的方法,一种石破天惊的活力,一种无中生有的发明。
然而环顾五四百年前后的文学及文学研究,早已经驯化为文化建构的一环。学院论述谨守分际,曰启蒙、曰革命,却无不似曾相识。但这样的现象不必意味“文学革命”到此告一段落,反而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五四文学的论述与实践的复杂面。我们并须挖掘“文学革命”所曾具有的潜能,以及被遮蔽的过程。

《五四与现代中国》会议现场
本文藉由鲁迅文论的两项观念,“悬想”与“神思”,探索五四文学意涵,以及当代的回应。这两项观念都强调“想像力的政治”:敷衍人生边际的奇诡想像,深入现实尽头的无物之阵,探勘理性以外的幽黯渊源。现当代文学主流论述以写实/现实主义挂帅,“神思”与“悬想”一向隐而不彰。却是新世纪以来科幻小説异军突起,提醒我们文学革命中这些被湮没的观念。又或者这不尽是历史的偶然。在20世纪初,鲁迅的文学事业即以翻译、改写科幻小説开始。而他早期文论也不断思索科学与文学的分野。

韩松
《狂人日记》一百年后,韩松出版《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2018),为新世纪以来方兴未艾的科幻小说热潮再添一本力作。韩松作品阴郁诡谲, 充满强烈末世隐喻。《医院三部曲》以宇宙的存在,就是医院为主题,写出另类“铁屋子”寓言,实在令人侧目。《狂人日记》与《医院三部曲》各据百年五四一端,形式极其不同,但都触及“神思”与“悬想”的多重维度,并展开隐秘对话:如科学与文学、身体与国体,疯狂与理性,疾病与医葯,入魔与除魅。更重要的,两位作家都藉此叩问书写与文学的根本意义,及其革命性真谛。

韩松《医院三部曲》
神思,悬想,圣觉
1907-1908年鲁迅在日本写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系列文章,思考维新知识分子面对西学衝击的因应之道。《摩罗诗力说》更进一步指出文学介入“人间情况”的枢纽意义。鲁迅强调“别求新声于异邦”。这样的新声非摩罗诗人莫属。摩罗诗人最重要的能量即在于“撄人心”。
摩罗诗人虽然来自异邦,鲁迅却将其谱系嫁接到中国传统,并以 “新神思宗”作为命名。“神思”源出《文心雕龙》,所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思理为妙,神与物游”。但鲁迅的用法则与欧西浪漫主义挂鈎,他心目中的摩罗诗人挣脱温柔委婉的“情”“ 志”传统,而淹然有郁愤之情,叛逆之志。相对于传统诗学的思无邪,鲁迅的“神思”极致处是“思有邪”。换句话说,新“神思”成为一种时代精反抗神的体现。相对兴观群怨,鲁迅要发出“真的恶声”。 另一方面,鲁迅又在古希腊文化中发现“神思”另一源头——神话。《摩罗诗力说》写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文学的不用之用在于“涵养人之神思”。《科学史教篇》肯定希腊“思理之士”, “研索天然”,不仅发现科学的“真源”,也同样见证“神话”的勃兴。也因此,在《破恶声论》里有了“僞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名言。

鲁迅以如此定义的“神思”来推动文学,内里的张力可想而知——而这也正是鲁迅文论的革命性所在。鲁迅晚年又提出“悬想”,缘起他对朱光潜治学方法的批判。在〈题未定草六-九〉系列杂文里,他讽刺朱断章取义,无视文本内外互涉的複杂关係。鲁迅讽刺当代“伪士”沉湎于历史层层斑驳积淀,殊不知倒果为因,反而失去体察历史本真面目——及其物质性——的能力:例如,希腊雕刻罢,我总以为它现在之见得“只剩一味醇朴”者,原因之一,是在曾埋土中,或久经风雨,失去了锋棱和光泽的缘故,雕造的当时,一定是崭新、雪白,而且发闪的,所以我们现在所见的希腊之美,其实并不准是当时希腊人之所谓美,我们应该悬想它是一件新东西。
如同“神思”“ 悬想”也是古语,意为挂念,又指揣测,猜想。而在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则强调悬想的凭空想像意义。鲁迅的解释更为复杂杂,因为他希望“悬想”所达到的,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历史真相的探究。换句话说,“悬想”反而拂拭了历史的积垢,还原历久而弥新的本色。而这一过程与其説是依靠知识分子的评头论足、上下考证,还不如説是有赖下里巴人无视历史的天真,对事物、对生活、本当如此的好奇。
“悬想”一词让我们联想鲁迅几乎三十年前所作〈科学史教篇〉里另一类斯关键词——“悬拟”。在文中,鲁迅虽然认知科学的重要,但不以经验主义,以及缘由内籀(归纳)法形成的实证科学为然。鲁迅提出“悬拟” (hypothesis) 作为调和,而“悬拟”关乎假设与想象,不仅如此,鲁迅文中对“悬拟”的把握是透过过赫胥黎的「divine afflatus」一词,并译为“圣觉”。
“悬想”与“神思”这些观念看似与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追求——启蒙、理性、科学——背道而驰,但鲁迅别有所见。在他的视野里,“神思”神游物外,以匪夷之所思引领叛逆想像,“悬想”出虚入实,搁置视为当然的成见,重新发掘事物的真相。两者都强调历史当下的无明与因循,无法以理所当然的科学啓蒙所解脱,而必须涉及想像力的介入,以否定辩证方式演绎人与世界的密切关係。这一介入的方法付诸实践,就是“文学”。
科学,玄学,与“悬学”
鲁迅以的“悬想”与“神思”所发展出文学观在五四时期及以后却并没有受到重视。现代中国文学的主流强调写实/现实主义,以文学作为反映世界,针砭人生的法宝。蕴于其下的科学语境不言可喻。学者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到郭颖颐(D. W. Y. Kowk) 等早已指出早期现代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倾向。当科学被无限上纲为解释并实践现代性的唯一法门时,其内容或实践的得失如何反而无关紧要。
唯科学主义论述在五四之后引起种种反思,以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科学与玄学(或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最为受到瞩目。论战最激烈处,丁文江直指张君劢及其从者为“玄学鬼”。与此同时,左翼知识分子如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提出唯物史观批判。
林毓生先生讨论“科学与玄学”论战指出,尽管这两派壁垒分明,但叫阵之馀,他们其实无视所共同享有的立场:那就是,他们都承袭了五四奉“思想文化”为解决问题的全权方法。他们的出发点或许泾渭分明,却都自认据有绝对正当性及合理性。尤有甚者,他们所根据的论述逻辑基本都是唯科学主义奉行不疑的归纳法。林毓生反问,在主观和客观、直觉和方法之间设下不可逾越的红线,他们果然能够将心目中的“科学/玄学”贯彻始终么?假设、拟想和想像仍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鲁迅早年弃医从文,对科学与文学之间的思考已触及日后科玄论战中许多议题。根据鲁迅早期文论的逻辑,我们有理由推测他对张君劢、丁文江理论的回应都不会苟同,却始终保持缄默。推而广之,如果文学曾是五四最受瞩目的论题之一,论战中文学的缺席,就更值得思考。五四推动文学改良和革命的两员大将,胡适和陈独秀,在论战中各据科玄一方,发表高论,但他们所论却丝毫与文学无关。鲁迅的沉默,和陈独秀和胡适的移转阵地,恰恰点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尴尬位置。
不论科学、玄学派,以及陈独秀所代表的唯物派,其实都是以“思想文化”为前提,作为解决中国危机的方法,却从未对其载体——语言、修辞、论述——有过任何怀疑。而就在论战的几年以前,他们所使用的白话文才因为胡适、陈独秀的鼓吹获得前所未有的注意。我们都记得,语言改革是文学革命的根本。语言改革最终的目的指向一套更新中文思考方式的教育政策,一种藉语言重现现实的模拟信念,以及一则以强国强种为前提的真理宣言。五四先锋们视白话文为“科学”而“民主”的透明工具。而在文学表征上,写实/现实主义小説被认为是直捣事物真相的重要发明。
鲁迅未尝不支持文字与文学革命,却早早看出其中问题。就在多数同行欣欣然运用白话文、新文学描摹社会、号召革命时,鲁迅意识到“文学”本身一方面被无限上纲,一方面却已经被视为当然,有若“无物”,而所谓的革命性已经成为工具化的藉口。
鲁迅没有直接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但他以文学的形式回应了论战的僵局。这包括了《呐喊》《彷徨》中诸多小説试验,《野草》等奇诡的散文诗歌,以及数量庞大的杂文。潘多拉的盒子既然打开,就无从保证结果。鲁迅何尝脱离他的科学训练,但他对事物的观察和设想如此“无微不至”,以致漫漶出丁文江式“归纳”法逻辑和幅度之外,暴露最散漫的生命物质性。他对玄学家所透射的彼岸世界其实好奇不已,但上下求索的“天问”反而逼出了更黑暗,更玄祕的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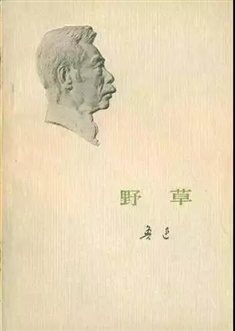
这是“鲁迅的”文学革命。这文学的革命性不仅在于亦步亦趋的反映人生,也在于直面人生晦涩的、难以穿透的物质性;不仅在于改变现状,也在于认知现状深处、无限“俱分进化”的动机。如果仅在写实/现实主义的脉络里解析鲁迅,其实局限了他文学观最激进面。套用科玄论战的话语,科学必以“神思”和“圣觉”为前提,而玄学不能自外“悬拟”和“悬想”。前者提醒我们任何斩钉截铁的实验必须有假説和想像的介入,后者提醒我们任何理所当然的“人生观”必须在历史与虚构交织的脉络中,反复接受检验。
然而鲁迅的想法较此尤为複杂。他的“神思”飞扬蹈厉,却终究弥漫鬼气;他的“悬想”无论如何要跳脱事物和思想的窠臼,縂似乎难以避免恶性循环。文学因此是科学与玄学之间粘滞飘忽,不能摆脱却也不能或缺的界面——“中间物”。这恰恰是号称一了百了的科学方法或玄学人生观所难以解决的。而“中间物”导向了更激进暧昧的“无物之阵”。
从“立人”的观点来看待鲁迅的“无物”,鲁迅的述作的确充满无所不在的虚无与惶惑。我们只能以“否定的辩证法”来证实他对生命和现实的关心。但与此同时,鲁迅已经一再暗示,跳脱“立人”的框架,文学革命者所探索的“物”的终末有无,才更慑人心魄——鲁迅是叩问一个科学与玄学以外的更广袤的世界。
是在这一层次上,“神思”和“悬想”所指向的虚无,也可以是来自无尽“虚”“ 有”的邀请。 “于天上看见深渊,由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文学主体是否要跨过理性或人生观最后一道防綫,成为文学最大的挑战。以此,鲁迅的“悬学”呼之欲出。
还是“在医院中”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学历经起落,基本仍奉鲁迅为宗师。但承续以上的论述,鲁迅文论中“悬想”与“神思”的面向,其实没有受到重视。文学史论述及一般批评所强调的,不脱大师感时忧国的块垒,或批判现实的精神。时至今日,以文学反映人生,改造民心士气的説法依然是主流论述,写实/现实主义敍事也依然是写作的大宗。
但在新世纪文学的开端,我们见证五四正统文学论述和实践疲态毕露。各种传媒的兴起尤其加速文学市场的式微——虽然“文学”作为“群治”资本的潜力未尝稍减。当此之际,科幻小说异军突起,十余年内引起全国甚至全球读者的热烈追捧,不能不说是新时代文学最值得重视的现象。
21世纪的科幻热潮并非前所未见,20世纪的开端已经有一次科幻小説勃兴现象。梁启超提倡“新小説”,心目中的理想文类就是科幻。而在本文的范畴里,所可注意的是晚清那场科幻热潮中鲁迅的脚色。这段时间正是鲁迅思辨“悬拟”“ 神思”“ 圣觉”的时期。1903年,当鲁迅翻译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时就提出他对乌托邦的想像。1905年,鲁迅译作《造人术》,想像“人芽”的生成,用以改造人种,更新国民。学者严峰、宋明炜都指出《狂人日记》透露科幻小説的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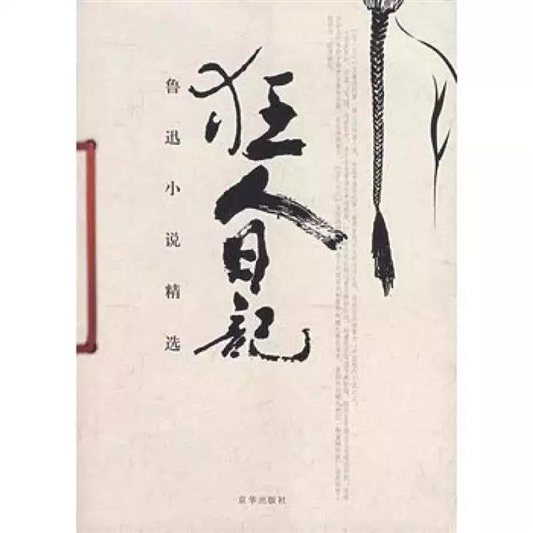
一个世纪后,鲁迅和晚清民初一代作者的科幻试验再度吸引读者。我们不禁要问,科幻文学在新世纪捲土重来,究竟意味什么?“悬想”与“神思”又能发挥是什么新的动力?本文所介绍的例子是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医院》、《驱魔》《亡灵》。在韩松看来,病、医、与药不只关乎厚生保健或“生命政治”,而根本就是人的生存本质。人人有病,人人治病,医与病、死与生不断轮迴,谁也不能出院。而作为三部曲的终结篇,《亡灵》构建了复活之日火星医院的“大同社会”,“ 药帝国”的崛起和崩裂暗示生命“原死” 就是“元死”。
韩松的《医院》种种立刻让我们想到鲁迅。的确,他有意识的向大师百年以前的感叹致意。鲁迅立志习医的经过我们耳熟能详。1906年幻灯事件以后,鲁迅放医从文,而他的逻辑仍然是医治身与心之别:“凡是愚弱的国民,卽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衆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
病、医疗与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鲁迅之后,沉疴重症蔓延作家笔下,被浪漫化、道德化、政治化、寓言化。在这一脉络里,韩松的《医院》三部曲又作了大跃进。宇宙即医院里,人人生病而平等。医院的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不断发现疑难杂症,百般治疗,让病人死去活来,继续住院。韩松曾经说“中国的现实比科幻还科幻”。的确,文学反映人生那套公式已是强弩之末,不足以刻画当下光怪陆离的现实于万一。 更有意义的是,韩松的写作不啻回应了鲁迅当年的“悬想”与“神思”。“悬想”让韩松跳脱敍事现状,审视医院运作的环节,竟然有了超现实况味,“神思”更驱使他将医院带向宇宙太空,从而投射后人类思考。有心读者不难从《医院》三部曲发现与鲁迅对话的巧思。末法时代的医院是个没有阻拦,却无所逃遁的“铁屋子”。而当病人和医生陷入重重互为主客——或互为主奴——的幻境里,那是“药时代”的“无物之阵”。
但韩松与鲁迅的对话不止于此。“悬想”与“神思”也不必仅作为社会或历史批判的方法。藉著庞大的医院神话,韩松其实重啓早期鲁迅对科学与文学的批判性思考。但韩松心目中的文学不再像青年鲁迅设想那般能够直指生命原相——而是“元”文学的不断自我指涉与解构。事实上,鲁迅作品从来内蕴极大的紧张性。摩罗诗人的“恶声”既能撄人之心,也能让人自啮其心。
回到本文开始的提问,鲁迅面对五四之后的科学玄学论战,可能的回应是什么?鲁迅当时保持沉默。而百年以后小説家韩松以《医院》三部曲再次提醒我们,鲁迅的志业是“悬想”,是“神思”,是文学。面对人所创造与被创造的生命诸多难题,文学以相生相斥的晦涩与清明,同成为病灶与解药。悬想跨越虚实 ,神思无中生有,两者都根植于历史内外的无物之阵,指向解放的可能,也沉思其不可能。科学与玄学派不会满意这样模棱两可的定义。但文学的革命性——及其自啮其身的反噬性——恰恰展现其中。
我们想到《医院》三部曲的开端。亘古永夜的太空里,三名僧人驾驶《孔雀明王》号太空船航向火星,他们寻找佛陀,看见医院。经过多少劫毁,三部曲的结尾火星医院出现一位女性,她来探究真相,陷入迷阵。她最后的希望繫于救援濒死的儿子——救救孩子。但真相可能就是幻相。“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曾如此默想。辗转其间,文学作者一如既往,他们知道那是一场未完的,永远不完的,文学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