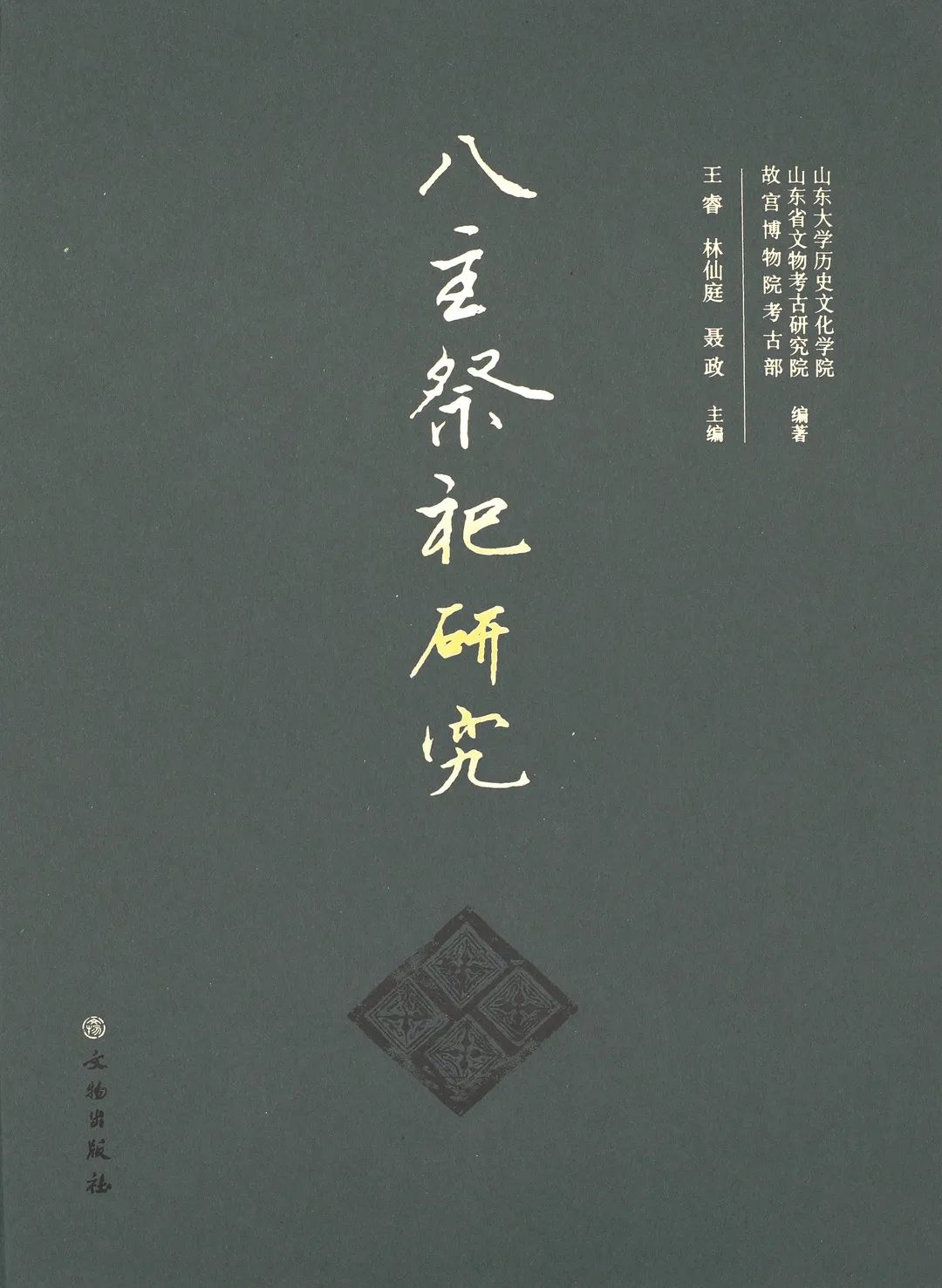|
按语
文研院自创立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跨学科交叉合作,为知识积累和思想创新提供学术支撑。近年来学界不少新著出版,其中一些书的想法或在文研院萌生,或曾在文研院得到了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学者的反复讨论。2020年,文研院微信公众号设立“新书推介”栏目,对和文研院有关学者的学术出版情况进行追踪和介绍。
本期新书推介栏目,我们介绍近期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八主祭祀研究》,该书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故宫博物院考古学部编著,北京大学李零教授为专书撰写了长篇序言。我们在此转发该书简介,及西北大学特聘教授罗丰为该书撰写的书评 “秦皇汉武的‘八主’祭祀:从考古遗迹看思想史的问题”。
中国古代祭祀遗址是关系到早期中国区域整合与宗教整合的关键问题。2019年3月23-24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曾举办会议“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围绕古人祭祀活动进行了专题探讨。
|
|
作者:袁一丹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目录
导论:秦汉祭祀的再认识——从考古发现看文献记载的秦汉祠畤
绪论 一、研究缘起 二、研究方法与工作过程 三、研究目的
第一章 天主祠 一、地望的考察 二、相关考古材料的搜集与整理 三、小结
第二章 地主祠 一、地望的考察 二、历史文化背景和梁父城城址 三、小结
第三章 兵主祠 一、地望的考察 二、现代蚩尤祠冢的调查
第四章 阴主祠 一、地望的考察 二、祠祀遗址的调查 三、历史文化背景和曲城城址 四、小结
第五章 阳主祠 一、地望的考察 二、祠祀遗址的调查 三、历史文化背景和三十里堡城址 四、小结
第六章 月主祠 一、地望的考察 二、祠祀遗址及其相关遗迹的调查与发掘 三、历史文化背景和归城城址 四、小结
第七章 日主祠 一、地望的考察 二、祠祀遗址调查与发掘 三、历史文化背景、不夜城城址的调查勘探和历年出土材料的整理 四、小结
第八章 四时主祠 一、地望的考察 二、祠祀遗址的调查与勘探 三、历史文化背景 四、小结
结语 后记 英文提要
秦皇汉武的“八主”祭祀:从考古遗迹看思想史的问题
随着考古事业的长足进步,过去学术界不便讨论的问题尤其是与古代思想有关的内容,现在有了重要的进展。从思想史的脉络来分析,一些原本不太清晰的古代中国信仰行为,在考古材料新发现的鼓励下成绩斐然。祭祀及有关事物如祖庙、牌位、礼器等作为氏族凝聚的象征;占卜询问的对象是久别的祖先,卜者扮演王与神的沟通中介;巫与神祇、祖灵等仪式,张光直都有讨论(参见张光直《美术、神话和祭祀》,郭净中译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页25-37;同著者《考古学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页6-10;陈梦家《啇代的神话与巫》,《燕京学报》,1936年20期,页458-576);郭店楚简、马王堆帛画和汉墓壁画的发现,使历史上原本已经失传的“太一生水”“太一出行”等重要概念获得新生(参见李零《“太一”崇拜的考古学研究》,氏著《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06年,页158-181;同著者《读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中国方术续考》,页330-342;冯时《“太一生水”思想的数术基础》,艾兰等编《新出简帛研究》,文物出版社,2004年,页251-287;邢义田《“太一生水”、“太一出行”与“太一坐”:读郭店简、马王堆帛画和定边、靖边汉墓壁画的联想》,《台湾大学美术史集刊》,第三十期,2011年,页1-16)。这些关怀的改变,一方面有赖于考古新发现,另一方面也与研究者兴趣有密切的关联。有些问题虽然重要而有趣,但研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一本以研究早已逝去多年并且为人罕闻的八主祠考古专著问世。
这部名为《八主祭祀研究》的考古研究专著,无论从田野调查的角度,还是解释考古材料的立场来说,都是一部有重要贡献的著作。自从著名学者李零先生关注古代山川祭祀以来,他极力推动相关学者对已知或未知的考古遗址进行调查研究,这本著作也是李零推动下的成果之一。本书的主编之一王睿关于八主祭祀研究一般性的看法和总结,已经在同名博士论文和文章中得以呈现(参见王睿《八主祭祀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同著者《八主祭祀研究》,山东省考古研究院等编《传承与创新——考古学视野下的齐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页400-411),现在这部著作显然是这一主题的延续。本书所包含的内容除去李零撰写的一篇精彩的导论外,共有十部分的内容,前一章是绪论,其后八部分是对所谓的“八主祠”的实地田野调查和发掘,最后一章是结论。在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作者采用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的方法,对秦汉文献中所记载的天、地、兵、阴、阳、月、日及四时等所谓的“八主”或“八神”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研究,因此这是一部由古代文献中宇宙观概念导入的关于祭祀遗址的考古学著作。
所谓的“八主”或“八神”的概念,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祭祀地点分布在今天的山东半岛。虽然它在秦汉国家祭祀体系中属于较重要的一类,是由皇帝亲自主导的中央祭祀活动,但是由于地处遥远,并不能像京郊太常祭祀那样每年举行。因此,《史记·封禅书》称:皇帝驾临则祭祀,皇帝不至则不祀,这样遗址的规模亦有不确定性。文献记录中亲临八主祠祭祀的秦汉帝王有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和汉宣帝,西汉成帝时八主祠祭祀才从国家祭祀体系中被裁撤。本书的主要内容大约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01 八主祠所在位置的调查或发掘
自从八主祭祀从国家祀典中废除以后,祭祀地点的主祠逐渐被人们遗忘,后世八主祭祀地点多有衍变,甚至祭祀内容也众说纷纭。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利用文献线索,结合出土文物,先后对山东半岛的有关八主祠可能存在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经过近四十年来几代人的努力,目下大体搞清楚了其中一些主祠遗址的所在位置。
天主祠大约在临淄故城南。城南牛山脚下原来有所谓天齐渊,泉水涌出如天之腹脐,喻为天下的中心,因以为祭,称“天齐”,原址已经被破坏殆尽。所谓八主的每个祭祀地点都与城邑或居邑有关联,临淄故城为齐之都城,有大小两城,大城建城不晚于西周中期,小城建于战国时期,过去出土的建筑材料中有“天齐”铭文瓦当。与封禅仪有密切关联的地主祠(参见赵超《释“天齐”》,《考古》,1983 年第 1 期,页67),调查时虽未能找到具体与之相匹配的祠祀地点,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试掘材料分析,应在泰山东南的梁父城附近。梁父城建于西汉时期,东汉废弃。
推测为齐祭天处建筑所用之瓦的“天齐”
兵主祠,主祭蚩尤,由于其所在的鲁西地区属黄河肆虐之地,早期遗址现已无迹可寻。现代的重建明显出于附会的需要,在古代遗址上大兴土木,不过足使当代的复建更具说服力。
阴主祠,所在的莱州三山是孤立于海岸的三座小山,地理环境不适于人居,地面上只采集到东周至北朝时期的遗物,祠祀遗迹不存。
阳主祠位于烟台市东的芝罘岛上,由于条件所限,祠祀遗址未能进一步开展工作。现尚存清代阳主庙的戏台等部分建筑,在大殿前曾出土过两组祭祀玉器。在芝罘岛大疃村山前沿海台地上,西北距玉器出土地点700米处发现东西长150米,南北宽40米的汉代遗址,遗物有汉代半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和陶器等,瓦当、铺地砖等建筑材料非一般民居所用,应该属于阳主祠的相关建筑。
“八神阳主庙记”碑文拓片
调查者对保存情况尚好的月主、日主祠祀遗址进行了细密的调查和发掘工作,得到了秦汉时期祠祀遗址相对完整的布局和组合形式。
月主祠所在地是归城,归城为当地莱人都城,始建年代不会早于西周中期,在莱国灭亡后还作为城邑使用,下限可能要晚到战国时期。月主祠位于龙口市归城外城内的莱山半山腰处,战国时期就存在建筑,西汉中期的建筑规模宏大,应属于较高等级。东汉至唐代多复修缮,现存石墙等建筑遗迹属于唐代。庙周家村的夯土台基上曾建有用于登临的亭台建筑,从遗物上可分出秦、西汉两个时代。建筑遗迹附近窑址烧制器物,与建筑遗迹使用材料形制相同,建筑材料或为当地烧造。
威海荣成市成山头为岩石壁立的海岬,曾出土商末周初和战国时期一些器物残片,可能为早期祭祀的遗留。秦汉时期建筑规模扩大,各类建筑错落有致、鳞次栉比。遗址虽然遭到严重破坏,但仍能从残迹中略看出功能不同的组合,包括亭(观)、立石、祠庙、施祭地点等。
四时主祠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台,经历年调查和研究发现,祠祀遗址由大小两个夯土台构成,参照阳主、月主、日主祠的遗址组合形式,琅琊台大台可能为祠庙和皇帝驻跸之所,小台最有可能临近祭祀地。经考古调查,大台的使用年代历经了秦、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等多个时期。另外,琅琊台西北的祝家庄遗址出土了“千秋万岁”瓦当、陶水管等建筑材料,器物的形制、纹饰与琅琊台出土的西汉中晚期器物相同,遗址周围还分布有西汉中晚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祝家庄遗址有可能为琅琊郡址,或为汉宣帝的驻跸之所。
另外,在临淄故城内在刘家寨发掘出土的封泥中有“齐祠祀印”,显然是官方设立专门祭祀机构的有力证据。
02 八主祠所置祭祀时间的推定
关于八主祠所置的年代,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已经说:“其祀绝,莫知其起时。”(《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页1367)所在的各个地点,战国晚期前均是异国所属,莱国于春秋晚期被齐所灭,阴主、月主、日主等祠祀才尽入齐的势力范围。泰山附近原本是鲁国的地域,齐人拥有则更晚。阳主所属纪国也是在齐灭之后纳入,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齐襄公伐纪,纪国灭亡。四时主祠在今黄岛区(原胶南市)琅琊台,曾属莒国,八主置时不一,很难确定。
直到齐国扩张到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时,八主的八个祠祀地点才尽归于齐域。原来分属不同诸侯国的各类神祇,这时才被齐国整合为八主祭祀。司马迁历数八神时,即以原来齐地为中心来叙述方位,所谓“齐地八神”的概念应该是战国晚期才形成的,这样八主祭祀的区域可分为泰山附近和胶东半岛。
中国早期的祭祀或与神灵、鬼神有关,甲骨文中祭祀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有关鬼神和神灵,向它们提出卜问,以求平安。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和上天沟通的方式已经发生变化,原有的系统已经无人能操作,才有孔子所谓礼失求诸野的局面。有关宇宙问题的思维理路及核心也发生了变化。战国时期在诸侯兼并的态势下,以求自保和发展的各国诸侯渴求人才,由此发展起来的诸子学说呈融合之势,其指向无一不是治国方略,正所谓“百家殊业,皆务于治”(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页427)。《管子》《吕氏春秋》《周礼》等可以说是学术思想转化为意识形态的代表作,以秉持的学术政治思想为基础构拟新型社会制度。八主祭祀虽然未能指认具体的创立者,但大致属于齐国稷下学宫中的黄老学派。司马迁将稷下学宫归结于一位事迹十分模糊的齐人邹衍,邹衍是稷下学宫重要成员,在诸侯中非常受欢迎。他所使用的“五德”术语即与“五行”相似,很明显包括一些物质元素(参见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页368-371)。他们不认同神创宇宙,宇宙观与金、木、水、火、土等元素联系起来,实际是自然观,有很深的阴阳思想。
03 由考古材料所得推衍出八主祭祀体系
中国的祭祀体系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祖先血缘系统;二是天地诸神。八主祭祀体系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中国传统上至为重要的人神系统的祖先崇拜,亦非单纯的某个自然神。它是东方思想家在经历了血缘分封制毁坏崩塌的离变之痛后,对于人、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以及人在自然环境中的地位所创造的神明体系。战国时期,血缘纽带关系变得薄弱,诸侯国间攻伐不止,灭国灭宗事件屡有发生,周天子只能维持其表面的“天下共主”的象征意义。面对靠血缘关系维持的和谐与秩序坍塌的社会现实,思想界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祖先祭祀之外寻求新的宗教支持。八主祠祀地点的选择是利用各地原有神祠来对应八主的祭祀对象,地点的方位分配也暗含着阴阳的划分。秦在血缘上并非周的“亲戚”之国,是由军功被封分,最初只被封为地位较低的大夫,勤王有功后才被迫封为诸侯,政权基础是论功行赏而非以血亲为基础的世卿世禄。商鞅变法中的军功二十爵被认为是秦统一六国的基础。汉承秦制,对王朝的控制不再依赖血缘关系,而是由地缘政治来主导,实行皇权下以郡统县的二级行政制度。
秦始皇谋求建立一个崭新的帝国,在许多方面形成与周天子完全不同的统治方式,他希望昭告天下新的时代来临。
他亲自巡视全国,但西巡和东巡的政治寓意完全不同,出巡西北可以理解为向秦国旧地民众庆贺,特别是宇宙神灵宣告统一。相反东方巡狩完全带有威慑性,即向被征服地区民众、神灵宣示征服。秦始皇曾下令将三万户迁移至琅琊台,设立琅琊郡的目标,显然是为了加强对齐地的控制,镇压齐地遗民。秦始皇抵达琅琊后非常高兴,前后逗留达三个月之久,十分罕见。所以秦始皇歌颂秦德的诸多刻石如泰山石刻、琅琊石刻、碣石石刻等都耸立在东方(参见柯马丁《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国的文本与仪式》,刘倩中译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页97)。大型祭祀活动是帝王沟通神灵的特权之一,《史记·封禅书》规定了各种等级的祭祀范围:“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页1357)秦的宗教政策是在保有和突出秦原有的宗教祭祀外,全面接纳原各诸侯国的山川祭祀,通过对神祇祭祀的专擅来标志对领土的占有。据李零研究,秦的祭祀结构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秦地固有的郊祀和东方齐鲁封禅(参见李零《秦汉礼仪中的宗教》,氏著《中国方术续考》,东方出版社,2001年,页144)。秦始皇东方游巡的目标在琅琊石刻中已表达得非常清晰:
东抚东土,以省士卒。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页245)
这样的铭刻都被置放在特定的场所,以使人们广泛知晓,也使文物印迹遗留在皇帝重要的仪式地,所谓巡狩的功能得以具体展现。
当然,秦始皇对东方仍有许多不放心的地方,术士观天象觉得东方有紫气,担心有取代者出现,所以他经常巡游的目标是要去镇压。在汉初人心目中齐地是重中之重,地位仅次于关中。田肯的一段话概括了其重要性:
夫齐,东有瑯玡、即墨之饶,南有太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汉书·高帝纪下》卷一,页259)
并说“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
秦皇、汉武利用巡狩、封禅来实施对东方的经略,他们对长生不老之术的痴迷,精研天地之奥秘和人事之废兴,练就了一些精通伴君左右政治生存术的东方思想家,这些人成功地兜售了他们的宗教思想。根据文献,天主祠未得到过秦汉皇帝的祭祀;秦始皇曾禅梁父,汉武帝至梁父礼祠地主。阳主祠所在的芝罘,秦始皇曾三至,秦二世曾从游,又于二世元年亲至,汉武帝也亲临。日主祠所在的成山,秦始皇曾二度亲临,汉武帝幸临的次数不详。秦始皇、秦二世、汉武帝曾多次到过四时主祠所在的琅琊。汉宣帝于寿良祠兵主,于曲城祠三山八神,遍祠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
日主祠、不夜城及其周边遗址分布图
秦汉时期的祠畤的主流大多延续了战国时期或更为古老的祠祀,雍城是秦汉帝国的祭祀中心,因为有先王宗庙和高等级的祭祀而成为圣都。将八主纳入之后,一些祭祀对象的地位得到提升。不过八主祠祭除宣布将东方祭祀体系纳入帝国的主流祭祀外,另一个目的则是在齐、燕方士的唆使下,以八主祭地为基点,向外寻求长生不老仙药,以满足他永生不老的意愿(参见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页74-81)。秦初的术士在皇室有着广泛的影响,秦始皇的向东巡狩至海上,明显是受到方士怂恿,让他求仙,他本人也满脑子神仙思想希望长生不老(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页9-12)。虽然他派韩终求不死之药并无下文,但他却将与上天沟通的祭祀权力牢牢地掌控手中,并形成以后的制度,即皇帝来则祭祀,皇帝不至则没有祭祀活动。祭祀的目标《汉书·天文志》说得很明白:“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而诸多的祭祀活动权力会下放到地方,地方诸侯祭祀即可,西汉初年的“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史记·封禅书》卷二十八,页1380)。八主祠祭祀的地位显然在名山大川之上,秦始皇开始的皇帝祭祀虽然表面上提升了八主祠的地位,但实际上却是由皇帝垄断与上天的交通渠道。“天齐”本是齐国原有的祭祀对象,“天齐渊”本为泉水,把它想象为天之腹脐来寓意天下的中心所在。此意念被借用至都城长安,在汉长安城外今人所称天齐塬上发现以一巨型坑为主体的遗址群(参见西北大学等《陕西三原天井岸汉代礼制建筑遗址(天井坑遗址)勘探简报》,《文物》,2019年12期,页4-8;曲安立等《陕西三原天井坑遗址坑底结构的天文意义初探》,《文物》,2019年12期,页49-52),为模仿“天齐”祭祀,挖坑以像天之腹脐来借喻为天下中心。这些祭祀对象的地位、祭祀内容与形式在不同时期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04 考古成果对思想史的贡献
本书作为一部考古学著作,我愿意指出它的一个重要贡献——完善而仔细的考古调查活动,再辅以对各种文献古籍的理解,不但对于理解古代建筑遗迹本身有所帮助,也在一些具体遗址的分析中,表达了对古人世界观内容的重要理解。
我们不仅仅要看到这些结果的重要性,更要了解考古学者如何通过自己本身的学科路径来关注已经逝去的古代思想概念,并且经过长时段的田野工作,使一些原本不很清晰的零星片段思想在考古遗迹的基础上获得阐发。诸多的遗址实际上需要在一种思想指导下进行通盘的整合。在这样的思路导引下,八处相关遗址经过考古调查被纳入同一框架内,完整的八主祭祀得以重现。而八主祭祀对于过去学术界来说是一个相当陌生的题目,无论秦汉史还是思想史。历史上有许多当时流行的思想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社会生活中被移除,也消失于人们的记忆之海。考古学的贡献在于当消亡的迹象重新出现时,我们有合理的诠释空间,使一些看似无序的内容获得有序的排列,发掘出一段历史思想的空白。这方面八主祠的发掘与研究无疑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结尾部分讨论了八主祠祭祀在秦汉时期二百年间的思想遗产,对后世祭祀活动的影响。
本书以讨论天、地、日、月、阴、阳、四时在宇宙论中充当构成要素和国家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变化,强调政治上的一元化和宗教上的多元化,作为全书的总结。这些内容也被用来安排人间社会秩序,在战国晚期和汉初的文献中都有反映。八主祭祀的废除,除去宗教因素外,实际上代表了皇帝对于神仙世俗性话题的有意减弱。如果说考古调查或发掘者本身已经意识到议题的重要性,又没有特别的理由放弃,类似的理解总结则尤显必要。
山川祭祀的正当性、神圣性在秦始皇时期就获得确认,但是他在区分重要性的同时将东方六国的八主祭祀提升到同样重要的位置,关东八主祭祀的神圣性得到捍卫。汉初政权继承这种传统,但在实际运作中却表现得并不平衡,以八主为首的六国祭祀体系使皇帝在巡幸时更具象征意义。汉武帝的目标恐怕是通过祭祀活动使统一的政治局面得以加强,这种东西峙立的祭祀格局在五岳四渎制度出现后被打破,汉宣帝最后对八主的祭祀举动,或许代表东方祭祀制度的终结。成帝时儒家人物已经占居要津,对皇帝产生重要影响,他们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国家祭祀制度。一些祭祀对象被移除或调整,所强调的理由是祭祀成本增加,国家经济不堪重负,实际是理念的变更,围绕京师长安新立祠庙是新兴祭祀制度确立的结果。
总的来说,王莽的郊祀制度显然是儒家思想完全占据上风的结果,他们透过郊祀制度建立儒家为主导的思想体系,而后者是二千年以来经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过去对于儒家的宇宙观尤其是反映在祭祀制度中的宇宙观呈现,了解程度有限,到底他们是直接诠释主张,还是透过郊祀传达其涵义,其中八主祠祭祀在国家祀典中占有多大的比重,过去并不十分清晰,只知道四时祭祀或承袭原有的内容;其他的祭祀则沦为民间信仰,祭祀活动则时隐时现,维持了很长时段。现在通过东方齐地的八主祠遗迹考古调查发掘,我们也有可能讨论从前模糊的一些课题。尽管从汉成帝到王莽制度确立之间,祭祀制度有若干反复,这显然是由于祭祀内容到祭祀地点在认识上的不统一造成的。最后完全成熟的郊祀制度在王莽朝确定,正月的南郊天地合祭是由皇帝亲祭,其余南郊、北郊祭由有司主持奉祀。祭天和祭祖的职能从此分开。
最后我们需要指出该书一些缺点,以尽评者之责。虽然本书贡献卓著,如果硬要指出书中不足的话,则在于面临的难题不少,尚有进一步再深入的空间。
首先,材料来源基本上是调查所得,发掘材料在其中所占比重很少。在有限的材料中,日常的生活遗物较多,可供明确断代的遗物较少,尤其是和祭祀活动有关的遗物。在时间上,从遥远的石器时代陶片到东汉建筑遗址中的砖瓦都有,当然这些都是由考古学科本身性质决定,但由于所要讨论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仅凭一般有限材料来讨论指向性非常明确的议题,显然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一些相当重要的、很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的文物,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讨论。例如芝罘岛中部阳主庙在房基下的土坑内出土两组八件玉器。出土玉器一圭、二觽,第二组玉器与第一组玉器器类、形制相同。出土在阳主庙的房基之下的两组玉器,大约很可能是汉代祭祀活动中被瘗埋下的,原简报中并未给予有价值的学术解读,这次的进步仅限于清晰的照片、线图和一般性的描述。早期祭祀的玉器与祭祀之间的关系,业经学界讨论,本书并没有有效地吸取这些成果。
书的最后明确指出,这种安排八主祭祀的政治思想理念,暗合了二百多年后王莽改制中确立的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郊祀制。当然这种说法并非由考古迹象本身推导而来,而是从八主祭祀的学理分析所致,明显超出一部考古著作要解决问题的范围。考古学应该如何介入思想史问题?虽然这样的讨论确实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如果冒险做出通盘性的检讨,则现有的考古材料并不能充分支持这种讨论。
中国考古学开始关注中国古代思想问题,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由祭祀入手来讨论思想史的主要问题也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我们进而可以关心古代社会中的思想演进这类重要话题。这些都有赖于学人的共同努力,我们期待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