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14期“机运的统治——政治中随机选择的消失与回归”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巴黎第八大学教授Yves Sintomer主讲,文研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段德敏主持,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李荣鑫评议。

本次讲座是在辛多默教授2023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The Government of Chance: Sortition and Democracy from Athens to the Present(中文版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基础上展开的。讲座伊始,辛多默教授首先介绍了“抽签”(sortition)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的复兴。他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欧盟的“欧洲未来会议”(The Conference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CoFE),其433个席位中有108个是由随机挑选的公民担任的。二是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了应对“黄马甲”运动而在2019年和2020年组织的“气候变化公民大会”(Convention citoyenne pour le climat),此大会的150个席位均由随机挑选的公民担任。三是墨西哥左翼政党莫雷纳(Morena)在2015和2021年的立法选举中用抽签的方式挑选了2/3的候选人。
本次讲座分为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辛多默教授梳理了政治史上抽签所发挥的角色以及人们对它的理解。他指出:从古代以来,抽签在西亚和地中海地区就得到了广泛的实践。比如,埃及东正教的教皇由随机抽签产生。辛多默教授表示,抽签在政治史上主要有三种用途:1)分配物品和社会职能(function);2)展示神的旨意;3)赌博游戏和其他科学用途(如抽样民调)。在雅典这个民主概念的发源地,抽签是用来确保政治上平等的重要工具。雅典人甚至发明了一种叫做“klérotèrion”的机器来进行抽签。抽签广泛渗透到了民主程序和雅典人的日常生活中,决定着土地、政治或司法职务等的分配,以至只有1/8的政治职位由选举产生而其他职位则由抽签决定。如伊拉德·马尔金(Irad Malkin)和乔西娜·布洛克(Josine Blok)所言,古希腊正是这样一个“抽签社会”(sortition society)。虽然抽签带有很强的仪式性,但古希腊人对抽签的理解则是高度理性化和世俗的。在一个高度竞争和流动的社会中,抽签可以为社会分配带来中立性(impartiality)并减少冲突,保证公民之间在形式上的平等。相较选举,抽签鼓励了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包容来自不同群体和立场的观点,是更加“民主”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就任用行政人员而论,拈阄(抽签)法素来被认为属于平民性质,选举法则属于寡头性质。”(《政治学》,卷四章九,1294b)

▴
古雅典抽签机器klérotèrion
在西方政治史上,抽签制度往往在共和制和民主制的语境下运作,一般需要和选举制度相搭配。辛多默教授认为,抽签在本质上是一种对权力、物品和职能的分配机制。和古希腊一样,抽签在罗马被广泛运用在政治职位、司法职位、宗教职位、学术职位、军事职务的分配上,并得到了高度的仪式化。抽签也和选举结合在一起,在不同执政官和其他高级政务官之间分配行省辖地。罗马人也发明了一种抽签机器,叫做“urna versatili”。

▴
古罗马抽签机器urna versatili
对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共和国来说,抽签也是一项常见的制度安排。在意大利,抽签制度自中世纪以来便盛行,并在进入近代之后向欧洲的其他部分扩散。比如近代早期以来的英、法、德,“黄金时代”(约15世纪开始至17世纪中叶)的西班牙,以及17、18世纪至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瑞士,都出现了抽签制度的痕迹。相较选举,抽签一般发生在小范围的精英团体内部。这种安排有助于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系统中选拔出最有能力的人士,同时限制派系之间的竞争和分裂。以威尼斯大公的选举为例,此流程历经十轮,最终在一个具有高度排他性的贵族圈子中选举出大公。这种制度虽然是一种寡头政治,但通过抽签保障了中立性以及成员之间的形式平等。值得注意的是,威尼斯的选举模式并不带有“审议”(deliberation)的性质——如下图所示,选举人在选举过程中并不能和他人有任何形式的交谈。

▴
威尼斯大公以及多数行政官的选举现场
同样在意大利,1494年,佛罗伦萨共和国在驱逐美第奇家族之后建立了“大议会”(Consiglio Maggiore, the Great Council;人数可达两三千人之多)。马基雅维利的同时代人、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 1483-1540)便为大议会实行随机选拔制度辩护。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圭恰迪尼将抽签视作民主,而选举则带有寡头色彩:“他们有更多的财产、亲戚和钱财并不意味着他们比我们更是公民;如果问题在于谁更适合统治的话,我们有相同的头脑、感受和口才,会败坏判断力的贪欲和激情则更少。”参与起草了现代瑞士之雏形——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c Republic, 1798-1803)之宪法的彼得·奥克(Peter Ochs)也为抽签制辩护。在1802年的一篇题为《关于抽签制使用的笔记》(“Note sur l’intervention du sort”)的通信中,他认为:“抽签本身就可以保证平等权利,将人们统一在一起,减少朋党之间冲突的混乱并平息公民的激情。”
抽签制度在中国古代也同样发挥重要作用。在明代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孙丕扬于1494年推行了抽签选官改革,进一步完善了“掣签法”——官员将根据抽签的结果分配到不同省份的不同职位上。这个被认为是公正无私且有助遏制腐败的制度得到了相当的好评,并一直延续到了晚清覆灭之时。中国的抽签选官制度并不独立运作,而是和其他制度(如科举)相搭配。这也涉及古代的“天命论”和基于功绩与才能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之间的争论。
综上,辛多默教授指出,人们选择抽签制度主要有三个理由:一是获取宗教的或超自然的启示,二是确保分配的公平中立,三是促进成员之间的平等。

▴
法国大革命: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卡纳瓦莱博物馆
法国大革命将欧洲的抽签制度和相应观念扫荡一空。在第二部分,辛多默教授将大革命年代抽签制度的消失归于人们“政治想象”(political imaginary)的转变。伯纳德·曼宁(Bernard Manin)在《代议制政府的原则》(Principle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一书中将抽签的消失归于两点:第一,现代共和国的建国者们(如美国立宪者)所想要的并不是民主政治而是一种“选举性贵族制”;第二,自然法观念的兴起也意味着“同意”(consent)这一观念在政治中起到愈加重要的地位,而选举则允许人们去表达自己的同意。在18世纪,无论是孟德斯鸠抑或卢梭都将抽签制和民主制、选举制和贵族制联系起来。而在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看来,抽签是一种过时的政治制度,选举则可以将最开化的公民挑选出来担任公职。这一基于“优绩”(merit)的对抽签制的批评极有代表性。
辛多默教授认为,抽签制度在大革命时代的消失,其可能的解释有三个。第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为欧洲人带来了全新的政治想象——理性、选择、意志、人民主权、自治成为了流行的政治观念。40年之前被视为可以遏制腐败和党争的理性的抽签制度在这个视野下顿时显得过时。第二,“代表性抽样”(representative sampling)的观念在当时尚付阙如,人们无法想象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可以产生对于总人口的“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第三,人们逐渐开始确信,政治是多元主义和冲突的领域,而这和抽签的原则相矛盾。辛多默教授认为,中国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类似的政治想象,这或许可以解释东西方在18世纪以来的“大分流”问题。
在第三部分,辛多默教授为我们介绍了抽签制度在当代政治中的回归。在学术界,抽签制度已引发诸多讨论。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菲什金(James Fishkin)教授指出:现代民主的缺陷可以从古希腊民主的两个方案中得到补救,即随机抽样和审议(deliberation)。澳大利亚的两位学者——琳恩·卡森(Lyn Carson)和布莱恩·马丁(Brian Martin)——也将抽签视为对民主的重要补充。他们认为:“政治中的抽签选举背后的假设是:任何想参与决策过程的人都可以做出贡献,而最公平的方式是给每个人平等的参与机会。”随后,辛多默教授介绍了“小公众”(minipublic)的概念。“小公众”是基于多样性(如性别、年龄、职业)对人口的代表性抽样,相当于一种“反事实”的民众意见,以最大近似于整体的真实民意。这个“小公众”也带有相当的“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也译作“协商民主”)色彩:代表可以面对面进行探讨,对公共事务进行细致的审议,做出理性的判断。在辛多默教授看来,政治中的随机抽签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一是上述的“小公众”;其二是陪审团制度,由于陪审团的审判只需要常识,因此不需要对总人口进行代表性抽样而只需简单抽样即可;其三则是雅典式的轮流统治的直接民主。
上世纪以来,在西方的具体政治实践中出现两波抽签民主的浪潮。第一波浪潮发生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这波民主浪潮的表现形式比较多样,比如有70年代首次出现在美国和德国的“公民陪审团”(citizen’s jury)制度,80年代发明于美国的“审议性民调”(deliberative poll)制度、发明于丹麦的“共识会议”(consensus conference)制度等。上文所述的“小公众”也可被纳入这波浪潮中。这波浪潮的特征是自上而下的抽样,且其组织是一次性的;虽然只是“咨议”(consultative)性质,但这种民主的确促进了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审议,增加了决策的理性程度。尽管如此,这波浪潮也受到了一些批评,譬如抽签筛选出的代表可能会构成隔绝于社会经济影响的小圈子,从而产生“民主精英主义”(democratic elitism)。第二波浪潮则更加制度化和赋能化(empowered)。辛多默教授指出,这两波浪潮在时间上其实是相互交叉的关系——第二波浪潮在第一波浪潮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嵌入到了公共治理的决策过程和正式的政治制度中。和第一波浪潮不同,第二波浪潮更带有草根属性,参与形式更多元化,更侧重政治参与和直接民主,并与现实的社会运动有密切的关联。文首提及的“欧洲未来会议”便可归于第二波浪潮。

▴
2022年欧洲未来会议会场
在第四部分,辛多默教授对不同形式的抽签民主的底层逻辑作了比较分析。辛多默教授首先对比了两种“小公众”的模式:陪审团(jury)模式和公民大会(assembly)模式。陪审团像是某种听证会,代表可以听取多方面的不同意见,不能或者几乎不能和外部的媒体、游说者相接触,并最终做出中立的决策。辛多默教授认为,这种模式可能更具合法性,但也许在政治上不那么有权力——因为其决策对政府来说没有强制力。爱尔兰制宪会议(the Irish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便属于这种模式。相较前者,公民大会模式则带有更强的“政治”属性和大得多的立法权能,它自身便是政治场中的行动者,积极地寻求改变政治和社会现状。这种模式无疑在政治上是更有力的,但其可能会由于过度的政治化而陷入争议。法国的气候变化公民大会便属于后一种模式。
随后,辛多默教授提出了三种当代西方“民主”的想象范式:审议民主、反政治民主(antipolitical democracy)和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审议民主是当代西方及学术界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辛多默教授认为审议民主本质上是和代议制民主相结合的,可以为公民的政治参与赋权,重建政府信任,遏制民粹主义,并有助于控制社会当中的权力/利纷争、导向和谐社会。第二种民主想象是所谓反政治民主。这种范式批评多元主义的代议制民主、社会自组织和社会运动,聚焦于社会和政治的共识性和治理性,将人民视作一个没有分歧的整体,如圣西蒙(Saint Simon)所言:“以物的管理取代人的管理。”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反“政治”(the political)的。而随着AI等技术的发展,它的实现可能性也越来越大。第三种范式是激进民主。这种范式在欧洲的典型代表是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和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激进民主主张以一种“敌对政治”(agonistic politics)来重新塑造社会的权力关系,以最终达到社会之解放。辛多默教授表示自己更青睐这种激进民主。他进一步表示,目前在欧盟设立某种永久的、具有立法权力的公民大会机构是有可能的且有必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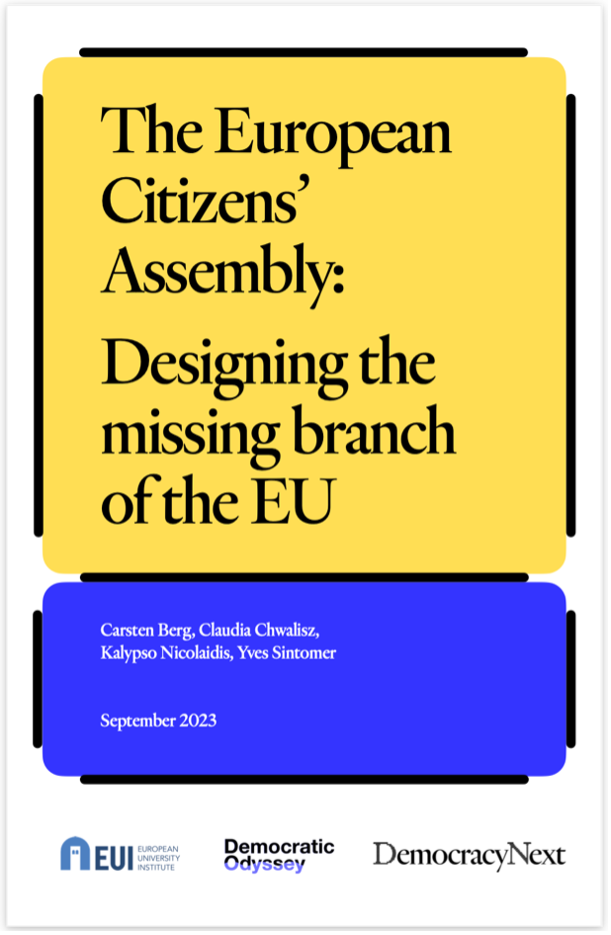
▴
辛多默教授及其合作者发表的关于成立欧洲公民大会的倡议
综上,辛多默教授对本次讲座的内容做了总结。第一,抽签在西方政治史上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而且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制度工具。第二,抽签的消失和重新出现都归因于政治想象的变化。第三,上世纪以来有两波抽签民主的浪潮,第一波是咨议性质的,第二波则为民众的政治参与赋权。第四,抽签在当代政治中的使用也有不同的逻辑,比如陪审团模式和公民大会模式,也有三种对于抽签民主的想象范式。第五,当代西方政治面临着结构性的危机,21世纪需要有新的政治制度来面对新的挑战,而抽签则应该成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变革中的一部分。
评议环节

▴
讲座现场
在评议环节,段德敏老师表示,抽签曾经是流行的安排政治生活的方式,但它在历史中“消失”了,而辛多默教授则将历史中的观念和实践取回,并放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的语境中进行重新的想象。段老师祝贺辛多默教授著作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表示期待北大出版社即出的中文版。
李荣鑫老师对本次讲座的具体内容作评议。在西方,将民主和代议制结合起来的历史非常短暂,而抽签是否可以被定义为民主的构成要素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辛多默教授对民主的定义可能有过于宽泛的风险。其次,抽签制度该如何落实在现实政治制度中也需要更细致的考察。最后,李老师回溯了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和审议民主的政治史。他指出,为什么抽签在民主政治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随后,辛多默教授对李老师的评议做了回应。他认为,民主的概念很有弹性,而他在本次讲座中的民主定义遵循的是现实世界的行动者们的政治观念。在西方的民主共和历史上,选举也只决定政治事务的一部分,政党领袖在候选人提名、官僚在公共政策领域其实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而他们的产生并不依赖于全民选举。辛多默教授也承认,“审议”这个概念在西方确实被过于宽泛地使用了。实际上,审议民主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概念,现实的审议民主实践依然是咨议性质大于审议性质。
在讲座最后,辛多默教授还和与会学者及听众就宗教信仰衰退在抽签制度消亡中的角色、抽签制度能否发挥更大的独立作用、18世纪以来小共和国的消失和较大规模的现代国家之兴起、当代西方政治秩序的危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